一張照片終結一場戰爭
文 張國治
甫於二○○六年年底於臺灣各大院線首映的《硫磺島的英雄們》(Flags of our fathers),在電視媒體或平面媒體上屢被介紹,片商似乎有意透過宣傳策略造成轟動一時之趨,然而即令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親自監製,並找來克林伊斯威特擔綱導演,票房上並未造成佳績,沒上映多久即匆匆下片。歌舞昇平之世,在臺灣對一般大眾看戰爭影片之現象,恐怕就有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5)所著的《旁觀他人之痛苦》莫可奈何的喟嘆!尤其屬於娛樂高消費群,在島嶼出生的新世代,草莓族群加上次文化加上蛋殼文化、流行及跟風,在戰爭焰火很難燒到自己跟前,大概很難想像戰爭究竟與自己何干?
《硫磺島的英雄們》講的是以少勝多的戰役,硫磺島是太平洋上一座火山熔岩冷卻後形成的火山島,雖是戰丸小島,卻處在戰略要津。它正當日本與美軍新佔領的塞班島之間。太平洋戰爭後期,成為日美必爭之地。美軍於1945年1月3日開始對硫磺島寶施轟炸。此戰役日軍被擊斃22000人,被俘 1000人;美軍為攻佔該島陣亡700人,負傷19000人。這個片子的故事敘述了美國士兵如何冒著槍林彈雨攻佔總面積不到台北市十分之一的硫磺島。內容敘述三位將國旗插在硫磺島上,幸運生還歸國的年輕戰士,他們的弟兄幾乎全部死在那座小島上,為了籌募戰爭公債,他們被政客操弄成了活廣告,一次又一次的在大眾媒體面前逼迫他們回想搶灘攻擊的那一刻,致使在身體與心靈上承受多次折磨。
金獎導演克林伊斯威特拍了兩個版本,一片為《硫磺島的英雄們》,另一片為《來自硫磺島的信》,除了美軍觀點外,還多了日本觀點。無論是美國或日本,戰爭對誰都沒有任何好處,被送上戰場第一線的年輕戰士,沒有一個人有把握自己能否活著回來。蘇珊.桑塔格在〈論戰爭攝影〉時就認為任何一個戰爭攝影師,基本上都是一個反戰者。那麼對於電影製片或導演製作一部所費不貲的電影,大抵也要揭櫫此一理念吧!克林伊斯威特強調,兩部電影內容不是描寫那邊正義或那邊邪惡,而是敘述戰爭對於人類以及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們的影響,更希望可以讓世人知道和平的可貴。「以戰爭換取和平」這是何等昂貴的代價!觀諸上一世紀,人類多次大戰役,回顧起來,無論發動征戰之侵略者,或被侵略、飽受壓榨肆虐之苦的國家,顯示了戰爭沒有絕對勝利輸贏可言,任何一場戰爭都是失敗,對誰都沒任何意義及益處,戰爭是無情的,上個世紀新聞攝影經典照片如越戰照片,就曾掀起美國人民反越戰潮,出身於西貢的尼克˙厄特 (Nick Ut 1951-)在1972年拍了《逃避美國凝固汽油彈的孩子》,光著身子被凝固汽油彈嚴重灼傷的照片,是曾經深深撼動人心的經典照片,提醒人們的記憶,二十世紀末美軍虐囚照片,又成為世紀末最新經典照片。
「一張照片終結一場戰爭」西門町捷運站內人行道牆面及戲院門口偌大電影看板書寫此一宣傳標語。一張照片,竟有如此巨大力量溢出?究竟為何如此神聖?是何種道理?
一場戰爭戰火,殘酷紀錄,經典照片美化了戰爭,美化了士兵,此一照片除了戰爭紀實歷史因素可堪探究,作為攝影史上的珍貴文獻,其照片究竟有何動人之處,捨其意涵背景之外,在攝影表現上有何高明之處,是否有其審美經驗自身俱足的地方?這都是可尋求、探究的。
依據Phaidon press Limited所編著的《攝影大師─500經典巨作》(The photography Book)第391頁對此張相片有如下的註解:「第二次世界已近尾聲,一群美國海軍在硫磺島的蘇羅巴奇山頂上豎起星條旗。你會覺得,好幾個人豎那一面小小的旗子,有點小題大作。他們的面部並沒有朝向鏡頭,實際上成了一些無名戰士,因而也是代表性的人物。本照片是個民族偶像,由於它的啟發,華盛頓才豎立起類似的雕像。不過,它也有更深的含義需詳加討論。這些人很像十九世紀以來愛德華.穆布里奇延時攝影裡那些志願者。這個畫面像是對於一個向前運動的人作多次曝光。穆布里奇對於藉著未來派攝影表現現代生活的動感有影響。這樣,羅森塔爾的主題,與其說是旗與海軍戰士構成的行動,倒不如說是時時在實現的動態事件。」這張相片取名為《硫磺島》(Iwo Jima),攝影者為喬.羅森塔爾(Joe Rosenthal)1911年出生於華盛頓. DC, 相片攝於1945年,正值二次大戰尾聲。註解論述中所提的愛德華.穆布里奇(Edward J. Muybridge 1830-1904)為英國十九世紀中至二十世紀初在近代攝影史有其深刻地位的攝影家,被稱為動態攝影家,他經常拍攝行進中的人或動物的運動,然後利用這些照片作成動的意象。當然這些照片亦可供畫家於素描繪畫時參考或生物學家研究採用,穆布里奇的相片除了動感連續性,頗具動畫(animation) 分格連接的效果之外,他的觀點毋寧更接近未來主義(Futurism)當年所預測的未來世界是充滿光影、機械文明的速度、動力、動態、音樂……的創作觀點。羅森塔爾《硫磺島》此相片的士兵是背著鏡頭,我們不易看到其五官容顏,不記是誰身影的無名人物,平心而論,無論就時間的宿命,天災人禍和人的無力,或人性深層而言,戰爭期間,烽火連天,誰記得誰?但重要的是他們是透過身影、肢體動作傳遞一個信念,其自身與他人融鑄構成一個大的結構體形成符號,並傳達其意義性。此外,其富有動感與張力的士兵動作,從構圖學上來看,經由我個人的解構,發現這四個士兵中,其位於畫面中間的三位與成45度傾斜的美國星條旗,恰若形成一個磐若金字塔的完美三角底座,但右下角士兵又能破此45度旗桿之限而逸出三角框架內,並朝右傾而向上,若再將此畫面由士兵手與旗桿交叉點及星條旗桿尾端作畫面水平分割,由下而上寬度比例漸小漸變,兩交叉三角形為其基本結構,並且令人詫異的是若從由筆者所繪的解構圖來看,這兩三角形的交叉點又恰為旗桿與左士兵手欲接近處,其巧合又不得不令人想起昂利.卡蒂-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經典攝影理論─「決定性時刻」(The Decisive Moment)哲學。無論拍攝者拍攝背景及經驗,此張相片實已構成所謂的經典性或代表性。其構圖之完整令人懷疑新聞照片在當下那一刻是否真實發生或是刻意造假、刻意安排,才有如此經典的構成之理由。
新聞攝影或紀實攝影中一些所謂的經典之作,經常有被質疑為刻意安排或造假來拍攝之說,如尤金.史密斯( W. Eugene Smith,1918-1978)一般的照片拍得都很美,很富戲劇性,他的一些攝影專輯(Photo Essay)如《西班牙鄉村》、《史懷哲》、《水俣》……等,用照片說故事的單元,至今仍被視為史上最難得的人性影像詩篇。他的《水俣》單元,《母親扶摟智子入浴》(1972),表現出悲傷的母親抱著肌肉萎縮畸形孩兒入浴,其畫面構圖莊嚴,令人感覺有聖母哀慟聖子像之姿,另一張題為《守靈》(西班牙村,1951)拍了哀悼死者守靈的畫面,其中親屬與死者構成的對角斜向構圖畫面之完美,直逼林布蘭特之群像構圖精髓,也曾令人質疑其畫面人物之構圖,是經由刻意編導出來?
另外瑪格蘭(Magnum)圖片通訊社的創始人之一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 1913-1954)其1936年西班牙內戰拍攝的《共和國戰士之死》拍戰士被機槍打中倒下的瞬間,被形容為有史以來最戲劇化的戰爭照片。其精準性,曾令人懷疑造假,至於最明確的造假新聞照片為英國朱根尼˙查爾德基(Jewgeni Chaldej, 1917-?)所拍的《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國會大廈上》,《攝影大師─500經典》第89頁亦有如此一言以敝之的註解:「看上去,戰爭將要結束,德國國會大廈下面的街道上,人影還在亂竄。你也有理由納悶,這兒到底發生著什麼事。因為,尖頂花飾光溜溜的,把旗桿插在上面根本不可能。即使插上去,下面的人也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旗幟。另一方面,幾個站立不穩的軍人與遠處檐頂屹立的雕像實在是渾然一體天成的圖畫。從我們這個角度看去,旗幟清楚可見,似乎暗示著這個場面僅僅是為了拍照而擺出來。這顯然是查爾德基導演的一幕。早些時候,一次戰爭中,他從一張撞球桌上搶出這面旗子,一直保留到戰爭最後日子,帶到德國本土,就為了拍出這樣的場面。這個故事符合一個普遍理解的概念:大名鼎鼎的戰爭照片不可全信。」大名鼎鼎的戰爭照片不可全信,新聞攝影史上許多指證歷歷如查爾斯基此一經典照片昭示著我們此一真理。
不管真實或造假,或刻意編導,那衹是照片呈現的方式之一,如果照片本身確是動人,還是會引人感動閱讀的。新聞照片並不是很好拍,尤其是戰爭照片,在殘酷的戰爭情景中又拍下非常具有美學中的形式力量,更是不容易。
但殘酷紀實的戰爭照片,不應該說是美化戰爭,美化士兵,這樣說似乎是有些嘲諷意味在,然而殘酷與絕美又何嘗不是經常不小心被撞在一起,並逬裂出動人情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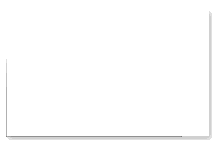





六月 24th, 2009 at 9:57 上午
我很喜歡這篇文章,作者談到了人性中對暴力的渴求與實踐,對於攝影美學與文化的影響。希望還有更多像這樣有深度的文章~
一點小小補充和作者與讀者朋友分享,作者認為硫磺島是場以少擊多的戰役,但在真正的歷史上,美軍動員了三個陸戰隊師(正規兵力70,000,加上輔助部隊可達110,000)才徹底擊垮日軍(估計18,500-23,000)的抵抗,無論如何都還是美國人佔盡陸海空優勢….
另一個小插曲,1944年原本美國海軍尼米茲元帥屬意襲取台灣作為對日本進行最後大規模登陸作戰的前進基地,但麥帥則屬意菲律賓,經過一番爭論後,台灣登陸作戰被束之高閣,只有在硫磺島登陸之前被美軍拿來進行反情報作戰,作為分散日軍兵力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