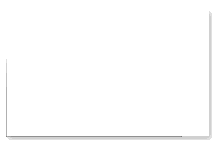溫習雲門(下)
文/盧健英
溫習雲門,有些舞碼成為經典,是基於其獨一無二的時代刻劃,它們在台灣人的記憶裡長青,可以描繪、討論甚至模仿,那就是《薪傳》。
一九七八年,長期經營舞團的精神壓力加上跳舞受傷,林懷民赴美國休息一年,在這一年裡,他更感受了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處境艱難,遙遠的中國成為夢土。回來後,他開始著手編《薪傳》,三十二歲的林懷民回想三百多年前,年輕的袓先如何雙手空空,渡海來台開創「做自己」的故事。《薪傳》是台灣戰後第一齣面對本土歷史的舞台作品。
<渡海>一折,展現的是絕不回頭的生命拚搏,鼓聲如浪,先民啟程,雙手合什,高高的舵手指向遠方,舞台上白布拉開滔滔浪水,未知的興奮與驚恐隨著旅程往情緒高點推送,落海了,救起了,險惡裡只有人與人的互相扶持。男舞者仆浪騰躍,在快速的鼓聲中做快速的前進,身體肌力的高度展現,成為一幕力與美交織出的波濤。在一個沒有布景的舞台上,<渡海>只用一塊素樸的白布便演繹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台灣海上移民史。
有些舞碼, 創作時是一種心理治療, 因為時代太過板蕩動亂,本是為特定事件而生,有特定的名字,但時間的長河拉開了之後,作品卻產生了獨立的力量,可以普世而生。
《輓歌》是一支悼念年輕生命的舞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全世界都聽見天安門廣場上的槍聲,在那個廣場上,年輕而充滿理想的生命一夕之間從中國的頂端摔下,改造社會的夢想碎裂。
由羅曼菲獨舞,舞台上,羅曼菲成為一個自轉的圓,她的頭時而仰望時而俯視,仰望時飛揚的裙裾宛如雲朵般地靈魂起飛,俯視時猶如秋天落葉在一場生命的旋渦裡,舞者必須在下墜的力量與上升的力量之間維持絕對的清醒,表現綿延無盡的哀傷與決然。這支舞成為已逝的羅曼菲最具代表性的影像,在羅曼菲過世之後,更成為一闕關於青春、美麗與消逝的短詩,而不只是那一個廣場上的紀念而已。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所有解嚴前的文化壓抑與禁忌像融冰般在街頭出現。六年級世代的年輕人迎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高張社會。同時,台灣用經濟實力在國際上冒出頭來,「做自己」不再是口號而是真實的擁有。每個人有了自己可以分配的自由與自己可以分配的財富後,理想狂飆的年代過去了。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黑手,把所有的人打散了。這位把國家社會扛在肩膀上的文化英雄,忽然失去了創作對話的對象。
有些舞碼記錄了時代風景,以及在都會與農村之間流離的邊緣台灣人身形。《風景》、《我的鄉愁,我的歌》看到滄涼荒蕪的都會現場與生活壓力下空虛無助的個人。 八○年代下半之後的雲門作品,顛顛倒倒,拼拼貼貼,踉踉蹌蹌。前面提及的《星宿》在後來的《夢土》裡扭曲變形,其他的作品裡則不時可見乩童的恍惚與狂亂。一九八八年,四十二歲,林懷民宣佈,十五歲的雲門舞集將「無限期暫停」,他離開玫瑰色的台灣,卸下「社會使命」,去旅行,這回真的要做自己。
一九九三年的《九歌》,是一個以屈原《九歌》文學為靈感而做的一齣歌舞祭天儀式,旅行回來之後的林懷民形容為他的「中年告白」,跳離現實台灣,他不講人定勝天,而講神鬼天地,天神世界的操控與撥弄,作品裡融雜了亞洲文化裡的各種原始或傳統的藝術色彩,包括鄒族音樂、 西藏梵誦、 印度西塔琴、日本雅樂、峇里島甘美朗等。
<雲中君>就是一幕騰雲駕霧的神祇出巡,由三加一位舞者攜手演出,三位一體形成的雲中君,以及一位腳踩溜冰鞋、圍著長圍巾執幡前導的卡通小子。<雲中君>的動作主要在表現「踩人」,因為人神間的遊戲規則是:只有神才能「踩人」。舞者吳義芳戴著神祇面具,聳肩擺頭,搖擺在兩位穿著西裝的現代人肩上,高難度的舉腿與翻越,他的表演舞台就是人肉肩膀與腰背,七、八分鐘不落地考驗的是高度的平衡感與三人之間的默契。十三年以來,至今沒有人可以代替這三位一體的組合。
復出之後的雲門舞集,林懷民的宗教感讓他用另一種眼光看台灣,他關心的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但只有「退一步」才看得到《九歌》裡的神祇世界。他也退一步不再用「台灣意識」去主導創作。一九九六年,太極導引大師熊衛加入雲門舞者的身體訓練,打破了雲門舞者的身體格局,如果說過去芭蕾或現代舞的訓練是「有為」的身體訓練,太極導引則在訓練「無為」的力量,它是由外而內「放鬆」身體的訓練,以呼吸導引動作,身體的自由度更大, 反而產生了一種如水般流動的身體美感。
五十二歲,太極導引系列達到成熟境界。一九九八年的《水月》是雲門舞集「太極系列」的里程碑作品。採用古典樂之父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的音樂,白衣舞者在水面與鏡面下,成為一幅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自然風景,一場中國人「鏡花水月終成空」的無為哲學。《水月》裡少有飛躍的身影,舞者如水草柔軟起伏,彷若照見更大的空間。
從太極導引之後,林懷民展開全面性的身體溯源,太極導引、靜坐,以及後來加進來的武術,讓林懷民找到定靜的力量。《行草》系列的第一次嘗試還似乎未脫描摹與呼應,但二○○三年的《行草二》及二○○五年的《狂草》,已經是一個書法精神層次的書寫,黑白分明的舞台上以留白、對稱、多對少、實對虛等隊形與空間的組合,呈現極富中國意境的人文境界。《行草》系列在中國的文化根底上創造世界通行的語言—對「美」的感動,哪裡是只跳給中國人看的舞?
二○○八年二月十一日,雲門八里排練場失火,燒掉了包括《薪傳》裡民謠老藝人陳達《思想起》的錄音母帶、雕塑家楊英風為《白蛇傳》所做的立體藤雕,以及許多數不盡的雲門表演紀錄資產。雲門在這座山上的鐵皮屋排練場待了十六年,在這段時間裡發展出穩定向上、顛峰發展的能量,雲門躋身國際一流之列、舞團行程預約到未來三年,二團持續地到學校、社區甚至醫院做示範與演出,舞蹈教室穩定成長。在他日復一日如耕牛般的工作與作息裡,二○○八年的這場大火,忽然打亂了編舞家「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日子。
一場大火,改變了六十歲的林懷民。
再弄一個排練場,很快,幾百萬元就綽綽有餘,繼續把雲門「該做」的事情做下去,完成該演的行程。「但,六十幾歲了,重複做這些事情對我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今天雲門就必須結束,那和五年、十年後再結束,能對這個社會有什麼不同?」
災後的第三天,台北縣長周錫瑋向林懷民推薦了與八里一水之隔,位在淡水河口的淡水藝術教育中心,毗鄰滬尾砲台和淡水高爾夫球場,佔地兩公頃。林懷民與一起踏勘的葉玟玟、張贊桃等一行人,一眼就愛上幾乎「像位在森林裡」的這棟水泥建築,更重要的是
,充滿台灣歷史源頭記憶的鄰居—滬尾砲台。
初春料峭的氣溫裡,一行人望向淡水河口,熱切的林懷民卻脫得只剩一件無袖汗衫,心中冉冉升起一個新的理想:「看遠,建立一個可以推動『專業‧教育‧生活』志業的永續基地。」
在這個環境裡,雲門雖然過得很辛苦,可是它是社會力所凝聚出來的一個團體。在十幾億人口的華人世界裡,它也是唯一一個長年在國際舞台上推陳出新的品牌。而雲門在九○年代發展出的三個板塊:一團、二團及舞蹈教室,涵蓋了從藝術性、草根性到社區性的表演,以至於舞蹈的生活教育與應用,都分別累積出完整的經驗。這些經驗如此可貴,林懷民說:「我希望我們能應用這些經驗,在淡水經營一座以表演藝術為核心的藝術教育創意園區。」
跳舞能改變社會嗎?如果雲門的舞曾經感動過三代的觀眾,去思考自己的來歷,改變自己看待困境的方式,那麼舞蹈不只是舞蹈,它可以改變人,改變社會。從二十七歲邁入六十歲,林懷民跳舞的方式,不只改變了舞蹈的社會地位,也改變了中國現代舞在國際上的地位。林懷民用舞蹈做了三十六年的社會運動,提示了年輕人歷史的重要,找自己的來歷,找自己的生命座標,做自己,然後創造歷史。
六十歲的林懷民,依然想改變社會。 你呢?
(本文改寫自2007年《溫習雲門—做自己》)
延伸閱讀:
知識地圖-雲門舞集舞作資產數位典藏計畫
http://content.teldap.tw/index/?cat=20&action=detail&id=164
雲門舞集舞作數位典藏計畫
http://cloudgate.e-lib.nctu.edu.tw/home.asp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