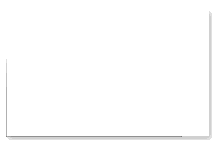通往記憶和歷史的道路-淺述國立臺灣博物館的數位典藏成果
如果將直立人(Homo erectus)視為人類起源的分界線,那麼,從第一個直立人出現開始計算,在地球所有時間的總和當中,人類大約擁有其中的200萬年。200萬年意謂著什麼?又容納了什麼?這個問號牽引著許多複雜的思考。
在不同的時代中,都有人試圖解釋時間:神學家將永恆指認為時間的終點;哲學家則以「存在」換算它,然後得到真理;歷史學家關照過去,聽見時間的絮語,堅守純淨的心靈與節制的情感來書寫過去的故事。如果,我們願意計算狂熱與奔放的部分,那我們將能看見在烈日下的暗房裡,有位藝術家正專注地描繪時間的臉龐。時間那連續不斷卻又難以追蹤的特質,使我們無法規範對它的感覺,它總是以想像式的速度流過人們的生命,可能毫無標示,也可能化為記憶之石;它能提供生命的線索,又或許會造成永無法辯駁的誤讀。
對現代人而言,為了穿透時間的屏障、更周延地認識世界,人們採集能以某種方式保存的歷史物質,根據各種智性或感性的系統,將之規則地收藏起來。也因此,人類社會在許多發展、建設的過程中都營建了不同性質的博物館,用以收藏一切改變或未曾改變的過去。博物館存在的任務之一,便是在一個穩定、固定的場域中,呈現各種流動的時空。它必須收納時間與空間,以及在這兩者之外的其他。
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博館),一字型的希臘式神殿建築就屹立於台北火車站周邊繁華的街區中,以它古典的線條,安靜而優雅地展示著島嶼過去100年的足印。1908年,日本政府為了慶祝南北縱貫鐵路全線通車並表彰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殖民政績,成立了「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館址設在今總統府後方的舊彩票局,收有上萬件藏品。1915年,新館落成,正式遷進現址,於1999年正式更名為「國立臺灣博物館」。這座博物館就像一扇窗戶,展開之後,我們得以看見台灣動植物、地質礦物、社會人文與藝術作品的點點滴滴。除了博物館營運的各項主要業務外,並致力於各種展示活動、教育課程、出版及各項合作計畫等,另研究與蒐集的方向可分為人類學、地學、動物學及植物學等四個領域。
日人設館的初衷,有一部分是為了展示殖民政府統治的威望,另一部分更是希望在蒐羅物件的過程中,對於台灣能有更深入的認識。「臺博館」從上個世紀以來累積了獨樹一幟的館藏質量、類型與經營傳統,無論是常設展覽或是階段性的特展,它都有其無法被取代的特殊地位。
我們可以理解的是,博物館以不同的展覽形式為物件標示價值與意義,透過詮釋與解說、展列的順序與次第、展櫃高低前後的設計、看板與動線的安排,博物館靜態卻權威地為觀賞者編寫出一部屬於該主題的教材,換句話說,博物館藉由展覽來建構知識的系統,領導觀賞者用特定的角度觀看歷史與大自然、分析或評價過去和現在。博物館進行這一連串工作的具體方式,勢必受到印刷術、視聽技術、軟硬體素材的影響,尤其近年數位科技與電子視聽產品進步神速,這些技術與設備更被廣泛地運用於展覽中,展覽的形式也已經與過去大相逕庭了。身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型博物館,面對這樣的新時代,除了開闢如「土地銀行」、「樟腦廠」、「鐵道部」等不同類型的分館之外,也開始思考更多發展的可能性。於是,從民國93年開始,「臺博館」決定投入數位典藏工作,並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支持,成為國內進行數位工作的博物館之一,舉足邁向數位博物館之路。以下,筆者試著簡述幾年來,「臺博館」所進行的數位典藏成果及內容:
人類學(Anthropology)典藏——台灣原住民文物
在台灣,原住民各種文物的收藏長期流行於民間與博物館之間,有為數不少的日常生活器具、傳統樂器、服裝或雕刻等收藏品,在時間轉演與市場流通中從部落裡消失,年輕世代的原住民青年們甚至鮮少聽聞關於這些物件的來歷,也難有機會理解它與祖先的關係,只能在一種模糊的情感當中,走進古董店、博物館或翻開各種教材、收藏圖鑑,默默沿著自己的血脈與這些藏品相通聲息。過去,以漢為尊的博物館或私人收藏似乎成為傳統部落文化沒落的隱性推手,但現在,博物館與私人收藏卻反而成為保存原住民歷史的方舟。會產生這樣的轉變,牽涉的不只是學術面與文化面,還有政治面的影響。
「臺博館」從日治時期成立至今,便歷經了這樣的路程。談到日本官方大規模搜集原住民文物的「盛況」,典藏管理組組長主持人李子寧[1]談到:「日本官方博物館對原住民文物的收藏,不只是學術目的,更多是為了呈現他們理解中的原住民。原住民就在這個關鍵時期被納入統治體系之下,分族分類的概念也是在日治時期透過博物館的展示而深化。在知識上分類,在政治上收編。博物館在這個層面上,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推手。」
多年來,「臺博館」定期展出這些文物,透過這些物件,我們依稀看見過去動盪的年代中,台灣島上聚居著不同族裔、不同國籍、不同階級且隸屬於不同陣營的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都藉著物件向我們娓娓地透露。即便這當中要探究的問題太多,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有了這些文物,台灣終於有機會在以漢族為主的社會中,為原住民族保留書寫歷史的空間,向社會介紹原住民們的智慧與心靈、文化演進與部落資產,同時提供人類學與民族學十分重要的研究材料。
為了使藏品資料更容易檢索並提高曝光率,民國93年起,在國科會支持下開始「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以分族進行方式進行數位化,至今平埔族、賽夏族、邵族、魯凱族、卑南族、鄒族、布農族、達悟族、泰雅族、阿美族與排灣族等11族皆已完成。該計畫將台灣原住民11族豐富的文物與資料透過嚴謹的攝影與色彩管理予以數位化,並建置網頁與檢索系統,與廣大社會共享這些文化財產。於是,博物館又在知識提供者的基點上開創了新的局面,不但已超越「展覽」這種傳統的傳遞方式,且將其收藏轉化為更加開放且親近大眾的資訊,這樣的做法同時也某種程度化解了博物館與原住民部落之間曖昧的、亦敵亦友的關係。一旦館藏更加開放透明,彼此便較能互相理解、互相看見,對此,李子寧組長補充到,「臺博館」近年與原住民文化團體接觸時,時常透過數位影像讓原住民更瞭解博物館有些什麼、又將會做些什麼,數位典藏成為博物館與部落溝通的媒介,也創造更多互動的機會。
耕耘了六年的時間,我們從網站上看見布農族的記事曆板上有先民生活的鑿痕,排灣族屋柱上那健壯的勇士雕刻至今仍是原住民青年最崇敬的形象,還有衣裙、胸兜、頭巾與檳榔袋,都是族群與部落之間各自的光榮標記。透過數位科技,網站使用者得以悠遊時間與記憶的走廊,對於原住民而言,這條走廊更是書寫歷史所必須仰賴的豐厚土壤。
動物學(Zoology)典藏——哺乳類、蜥蜴亞目、蛇亞目與甲殼類標本
1860年代,英國博物學家斯文豪氏(R. Swinhoe)奉派來台擔任英國駐淡水副領事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展開台灣自然生態的考察。斯文豪氏多次進行環島平原地區的生態調查,他尤其鍾愛鳥類與哺乳類,曾在論文《福爾摩莎哺乳動物學》(On the Mammals of Formosa)中描述台灣黑熊、雲豹等哺乳動物的生活習性,其鳥類專文《福爾摩莎鳥類學》(The Ornithology of Formosa or Taiwan)更記載了187種台灣鳥類。斯文豪氏的論文可以說是台灣動物研究極早期而且完整可信的文獻,可惜斯文豪氏所採集到的標本皆送往歐洲,大部分收藏於大英博物館中,並沒有留在台灣。進入日治時期後,日人在台成立大學、博物館、農業與林業試驗場等相關機構,採集的標本才得以留在台灣,成為我們今日寶貴的資產。當時著名的博物學者如鹿野忠雄(Kano Tadao)、堀川安市(Yasuichi Horikawa)、素木得一(Tokuichi Shiraki)、黑田長禮(Nagamichi Kuroda)等人在台灣各自展開地理、動植物、原住民族及地質等等調查工作,採集之標本成為台灣日後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
在動物部分的標本,除了台灣大學、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等處之外,「臺博館」掌握日本官方收藏的龐大資源,不只擁有豐厚的人類學文物,大量的動植物標本也讓該館成為台灣第一個具有自然史意義的博物館。其所收藏的標本共計31765 件(涵蓋鳥類、哺乳類、爬蟲類、兩棲類、甲殼類、昆蟲類等等)。其中以鳥類及哺乳類蒐藏最豐富,除了瀕臨絕種的珍稀標本之外,更包括雲豹、水獺、黑長尾雉、藍腹鷴、寬尾鳳蝶等台灣特有種、特有亞種及保育類動物,在生物多樣性或動物相的研究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
每一個標本都伴隨一筆資訊,但這些標本若只是置於庫房中,就只是一些零散的訊息而已;在庫房冰冷的架上,我們無從得知儒艮與鯨魚、雲豹與山貓等不同動物之間的關係,也就無從拼湊出生態全貌。博物館的任務是透過有系統的分類與展示、研究與比較,將這些各自獨立而且封閉的資訊單元串連起來,整合成可用的知識。然而博物館有限的空間卻大大影響博物館展出「原件」的機會,導致社會大眾與館藏之間始終存在著強烈的陌生感,甚至有「下次再看到同一件標本展出,可能是50年後了」的無奈。為了突破此一限制並延長標本的生命週期,動物學組自93年開始進行標本數位化工作,陸續完成哺乳類約400筆、蜥蜴亞目將近800筆、蛇亞目約800筆、兩生類約615筆及甲殼類700筆的標本資料[2],資料中包含其物種分類與標本資訊。
這些標本歷時久遠,加上館方各時期管理與清點方式的差別,在數位化過程中必須克服標本本身的損害與資料缺漏誤植的問題,以「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甲殼類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為例,許多甲殼類浸液標本保存狀態已不如往昔,有些甚至足肢斷裂、禁不起反覆碰觸,於是將標本逐一修整並重新校正的工作顯得極為重要,計畫主持人林俊聰說:「拍攝時標本依然要浸泡於酒精當中,以免乾燥損壞,常常一整天拍下來,助理們都醉了。」
此外,拍攝時更必須精密掌握標本的細節,以提高標本資訊的可用度,如拉都希氏蛙與古氏赤蛙兩種蛙類乍看類似,這時就要透過其體型、紋色、皮膚隆起程度、側摺型態等細節來分辨,計畫團隊若在數位化過程中遺漏了這些細節,這兩筆資料的參考性當然就降低了。
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每一個數位化的環節都以不同的程度影響著人們對於台灣動物相的認識。當使用者透過該「臺博館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的「聯合目錄」實際檢索這些標本照片時,定能深刻感受這一點。
地學(Earth Science)典藏——貝類標本、礦物與化石
對於地球科學這樣的學科來說,實證是基礎的要求。無論是岩石、水文、土壤或古生物的狀況,想要深入瞭解,都必須深深依賴岩礦、化石、標本或是測量數據彼此交織所得的資訊。亦即地學研究必須仰賴確實的證據,這些證據幫助科學家們將地球的各種面目建立起來。
「臺博館」典藏的日治時期地學標本以堀川安市所採集居多,光復後的收藏則以林朝棨(1910-1985)教授所採集的標本為主。林教授是第一位台灣本土培養出的地質學教授,對於台灣地質研究與許多重大建設皆貢獻良多。林教授任職於台灣大學地質系期間,帶領學生一槌一鑿地踏察山林與地層,熱烈投入地學研究,即使因涉水過多造成下肢長年神經性風濕、因搬運化石導致脊椎傷害,林教授依然不離不輟地工作,直到退休。「臺博館」除了藏有林教授當年所採集之一部分標本以外,也收藏有日治時期以來各個時期、不同日本博物學者所採集的標本,每一件礦物化石、每一張採集標籤,都是以熱情和毅力所留下的台灣地質證據。「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礦物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主持人方建能帶領我們參觀庫房,他談到在整理標本時,每一件標本上面的採集標籤與記錄標籤雖然老舊,但計畫團隊都捨不得將之從礦石上刮除,這些標籤有的是用黏貼的,有的是直接寫在石頭上,甚至習慣將小紙片捲起來塞進貝殼深處,這都是歷史的一部分,不同採集者透過標籤展現特殊的個人風格,這些都應該被保存下來。正因計畫團隊採取這樣的做法,我們在檢索照片時便得以連標籤及記錄痕跡一起瀏覽了。
民國94年,地學組展開「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貝類模式標本及淡水貝標本數位化計畫」,接著連續兩年獲得補助,陸續完成了貝類模式標本正模39件、副模2件與淡水貝類、腹足綱原始腹足目、腹足綱中腹足目等近5000件的標本數位化工作。在礦物部分,從96年開始至98年度「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礦物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完成為止,總共建立2000餘筆的礦物資料。計畫網站中以標本類別分層排列,使用者可以選擇直接檢索,也可以選擇逐一點閱,這樣的設計滿足不同專業程度的使用需求。
植物學(Botany)典藏——維管束植物、海藻與苔蘚類標本
因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洋板塊相互擠壓而形成台灣山脈、縱谷、盆地、台地及沖積平原等多樣化地形,島嶼面積雖只有3萬6千多平方公里,然因北回歸線通過,加上高達海拔3952公尺的山地,使台灣擁有熱帶、副熱帶、溫帶與寒帶等不同氣候特徵。複雜的氣候為台灣帶來多樣性的植物物種與植被種類,讓台灣成為植物多樣性的寶庫。「臺博館」植物標本館收藏有維管束植物、藻類、苔蘚等標本,其中包括臺灣的維管束植物標本、週邊海域海藻標本及採集地遍佈五大洲的苔蘚植物標本。這些植物標本同樣歷經長久的時間、涵蓋不同地理範圍,是台灣植物與生態研究不可缺席的重要資源。
這些標本資源不但可以做為生物研究的材料,同時也具有歷史的意義。植物學門的數位典藏工作從民國93年開始到95年為止,連續三年透過「國立臺灣博物館植物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總共完成約8000筆標本資料,包含維管束植物約5000份、海藻約1800份、苔蘚約900份,全數皆已匯入網站中供使用者瀏覽。
當代博物館表徵,一方面是博物館實體自我發展結果,博物館社群已不只將問題圈限在收藏、教育、展示之實務;另一方面,博物館呈現的方式受社會文化定義,是一種獨特的建構。[3]
在文明社會中,博物館扮演許多種角色,它展示某些歷史、梳理知識與知識之間的關聯、賦予古文物現代性的詮釋,與此同時,博物館更與社會產生互動,在互動中型塑彼此、改變彼此。過去,人們旅行,前往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美術館、標本館或任何形式的文物館參觀,研究人員在這裡獲得材料與養分,而遊歷各地的旅人在這裡將他們心中的世界拓寬。那現在呢?在變動的世界中,博物館要如何成為社會文化機構的一部分、提供社會大眾新的博物館經驗?同時,它又要如何回過頭來重新觀察自己的形狀、審視手中那把知識的權杖?這一連串的問號在博物館界中已經引起諸多討論,「臺博館」當然也在思索著這些問題,它同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館一樣,必須面對不同於過去的資訊流通模式。
數位典藏因此成為一個新的選項。首先,藏品能夠以美觀、真確的標準被翻攝成數位影像,並分別以不同的角度拍攝,成為一「組」藏品圖片。接著透過網路軟體等技術,使用者坐在電腦前就可以直接觀看這些圖片,視需要拉近、拉遠、捕捉藏品的細節,甚至下載收藏。
這樣的經驗與過去親身蒞臨博物館、觀看囚禁於玻璃櫃中的展示品相比,這些物件對人們來說已經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這是第一次,展示品在沒有地心引力的狀態中呈現眼前,隨著電腦的發達,我們的視角也被打開,可以用新的形式、更加方便且迅速地擁有無遮蔽的視線來觀看物件,360度環物、3D透視、局部縮放、互動式資料庫、數位學習,種種高便利性且不受時空限制的典藏方式,在數位世界中都不會成為難題。這就是博物館在進行數位工作之後,提供給社會大眾的全新經驗,這個經驗不只有「觀看方式」的突破,還使博物館從「冥思的殿堂」轉變成為「教育者、創意者」[4]。
此外,博物館在知識的規劃上也因為數位技術的來臨而有所變革。對於研究者來說,重要的不見得是藏品本身的面貌,而是每一個透過藏品展露出來的訊息。因此「收藏」不再只是收藏「物件」而已,人們已經擁有足夠的能力來收藏「物件產生的脈絡」。接下來迎接我們的,正是一個原件與數位影像相互補充的新博物館時代。李子寧組長談到:「傳統的博物館不收藏影像,早期只是當成備份的檔案,也就是以器物為主。但現在往回看,早期的一直到民國時期的影像紀錄,卻成為博物館缺乏的部分,不只是類別上的缺憾,也無法輔助器物的陳列。」有鑑於此,人類學收藏已經日漸重視影像的收藏價值,比方說,除了收藏某位原住民藝術家的藝術作品之外,也能以攝影機錄下他創作的過程、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家人與故鄉等等更多形構創作者心靈與力量的元素,作為我們解讀、欣賞該件藝術作品時的先備知識,這些重要的補充材料幫助我們探索物件的來源,瞭解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每一個影響深遠的片刻。
物件是記憶與歷史的道路,不同的物件之途通向迥異的世界。[5]
博物館所收藏之物件與標本就像造路之石,一塊一塊相接鋪陳,砌出通向記憶、歷史與生物多樣性的道路。觀察「臺博館」數位典藏的成果,再對照該館今年度開館啟用、並定位為古生物館的土銀分館,我們可以看見一座博物館的轉變,無論是物件展出形式、展示規畫的主題、展示空間的營造甚至是博物館與參觀者之間的友善關係,這座位於寧靜公園與繁忙街區之間的博物館,已然成為過去、現在與未來等不同時空的交會場所,為我們妥善收藏那些無法被記憶所容納的點點滴滴。
◆文章中圖片感謝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註1 註1.李子寧先生同時也是「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主持人。
註2 註2.除了95年度「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兩生類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支持外,93年度「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哺乳類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94年度「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蜥蜴亞目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與95年度「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蛇亞目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皆由國科會補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