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稿》淺談台灣官方美術機構數位典藏的功能與責任
楊浤淵╱撰
 2009年,當代藝術操作媒材與議題的交混、混雜(hybridity),憑恃跨領域(multi-field)、跨學門的結合來再現我們所身處的當下,今日早已屢見不鮮。但是,觀看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和高雄市立美術館的數位典藏之內容(作品種類與風格形式)與形式(數位化技術與互動性設計),著實與當代藝術所表現出的後現代交混大相逕庭!再說,相較於商業藝廊的網站,官方美術機構網站的訪客群可是遍及社會大眾,當民眾意圖上網查詢展訊與藝訊時,它們必是搜尋的熱點,想而知官方美術館官網的訪客流量不會少。換句話說,官方數位典藏館的知識分享對於我們社會的藝文教育與推廣,有不可言喻的功能與責任。於是乎,清楚台灣官方美術機構所主導的數位典藏之於典藏機制與數位技術的關係,成為本文明晰正在持續進行的當代藝術數位典藏「效.益」之關鍵。
2009年,當代藝術操作媒材與議題的交混、混雜(hybridity),憑恃跨領域(multi-field)、跨學門的結合來再現我們所身處的當下,今日早已屢見不鮮。但是,觀看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和高雄市立美術館的數位典藏之內容(作品種類與風格形式)與形式(數位化技術與互動性設計),著實與當代藝術所表現出的後現代交混大相逕庭!再說,相較於商業藝廊的網站,官方美術機構網站的訪客群可是遍及社會大眾,當民眾意圖上網查詢展訊與藝訊時,它們必是搜尋的熱點,想而知官方美術館官網的訪客流量不會少。換句話說,官方數位典藏館的知識分享對於我們社會的藝文教育與推廣,有不可言喻的功能與責任。於是乎,清楚台灣官方美術機構所主導的數位典藏之於典藏機制與數位技術的關係,成為本文明晰正在持續進行的當代藝術數位典藏「效.益」之關鍵。
官方機構的典藏機制與數位典藏
典藏,是物理實存的原作收藏。然而當代藝術如此多元豐富,台灣的官方美術機構當然無法典藏入庫每一件質優的當代藝術作品,再說也難以針對性地為每一件作品生產專屬於它的典藏模式。想當然其中不少作品因為超乎官方目前的典藏能力,遂無法成為官方典藏的可能選項。反過來說,官方往往會根據美術館自己的風格定位與認知分類(genre)來選擇典藏標的,採取策略的典藏選件以利入庫後的收藏,無疑典藏的過程中必然的作業機制。
想來著實可以理解何以官方和私人典藏機構都偏好典藏平面、立體,以及近年興起的錄像。箇中原因無非就是媒材傳統的油畫典藏只需考量溫、濕度,同屬平面的攝影亦然;雕塑、裝置與陶藝等作品基本上只要有充裕的典藏空間,頂多再留存作品的圖稿,以利公開展出的擺設;典藏錄像看似純粹保存母片,但典藏機構需要展出時,就會有公開播放時的影音要求、作品版數直接影響的作品價值之疑慮,以及為避免消耗原作而拷貝複製的智慧財產權問題。因此,大概除了像位於德國卡斯魯爾(Karlsruhe)的ZKM媒體藝術中心這類國家型藝術機構,典藏錄像的市場明顯保守。然而,正是因為這些藝術類別的方便典藏且擁有市場,它們很自然地就成為民眾和官方所共識認知的當代藝術。但反過來說,不就表示會不斷地產生因形式而不受官方青睞典藏的遺珠之憾。台灣官方美術館的數位典藏館之內容,正一步步逐漸走向均質!
〈德國卡斯魯爾ZKM媒體藝術中心錄像藝術檔案資料庫〉,圖版來源: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現實的情況,目前台灣的官方美術館也確實沒有能夠收納各種範疇的當代藝術之庫房與設備,不少作品註定與官方典藏無緣。縱使硬體設備允許,於此前題還要能通過官方推派的審查委員之選件!他們對於當代藝術的主觀認知,或說代表的官方喜好更是影響作品能否被欽點入庫的要因。說來,若沒能符合官方需求或得到「台北獎」、「高雄獎」等官方獎項的肯定,許多當代藝術作品相當容易就礙於形式,別說要被官方收錄到它們的數位典藏資料庫,光要被典藏入庫就難上加難。不過,對象若是享譽國際的名家代表作,輔上合理的價格、合宜的體積、媒材的講究再加上易於長久保存的話,那它是很有機會為官方美術館所接納。但是,若放任這樣的典藏機制繼續進行下去,未來不就註定只會有經典款式的當代藝術能夠滿足官方的典藏需求與選件標準!?
數位典藏,簡單說就是典藏機構它們將庫房的藏品進行數位化留存與應用的機制。經過數位化後的作品自然就成為館方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產,轉換為數位規格的它們當然就可以透過網路的傳播讓作品的能見度提高,藏品不再只有公開展出時才能現身。數位典藏的目的不單在建立資料庫,還必定會在網路上構築數位典藏館,進行藝文的教育與推廣,才能發揮數位典藏的價值。無庸置疑,網路媒體它那數位虛擬的特質,讓每一美術機構的數位典藏館有如一間間任何民眾都可前往觀賞藝術品的藝文空間,其展覽性消彌殆盡了藝術品此時此刻擁有的儀式性「靈光」(aura)。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談及攝影的複製技術對藝術品本質的影響上,就說道:「藝術品的功能不再奠基於儀禮,從此以後,是奠基於另一項實踐:政治。」[1]網路的出現更加強這事實,藝術品的影像(照片)已不再只能透過實體的照片流通,現在不過上傳至網路這簡單步驟,就能讓藝術品的影像(數位碼)發散出去,網路讓數位典藏更易於施展它的政治功能。毋疑,現今社會大部份的民眾都有在使用網路來獲取資訊的生活習慣,若經過適時的宣傳與推廣,虛擬美術館(數位典藏館)可吸引的觀眾群與年齡層絕對在實體美術館之上。不置可否,藝術仍舊難以擺脫自文藝復興以來所代表的階級意識,但數位典藏確實讓文化的訴求對象不致於偏向知識份子。換句話說,數位典藏所背負的藝術教育與政治責任,絕對是不下於實體美術館甚至是超過,效益不可輕忽。
顯然,參照官方典藏的情形來清晰數位典藏的現況就有所必要。從官方的北美館、陶博館、國美館和高美館正掛在官網上的數位典藏看來,北美館二十五年來共有超過四千件的藏品,但它的「典藏數位資料庫」內容竟然大多數為繪畫、攝影、影像和雕塑、陶藝,我想它庫房裡的藏品雖必然偏重典藏這些作品但也一定不止這些範疇。當然,不單典藏的選件會影響數位典藏的內容,亦可能因數位化作品的技術著重在使用高解晰攝影,致使數位典藏館的功能只能偏重在資料查詢,似乎無意追求有如原作般在網路上的再現;乍看之下鶯歌陶博館的數位典藏館似乎就完整多樣些,很多作品在數位互動上不止能縮放細節還可以立體翻轉觀看作品的影像,唯可惜數位典藏的內容幾乎為單件(組)獨立的實用陶和創作陶,不見傳統形制外的「當代陶藝」。或許我們可以詮釋這結果是在提醒尚未將塑性強大的陶土運用到極致,也可能這就是官方對於陶藝的認知!?詳細情節難以說清,但至少可從陶博館的數位典藏看出當代陶藝所背負的傳統包袱比我們想像中還重;高美館的數位典藏亦不遑多讓,數位典藏的內容就是文字和影像,更別奢求在線上全面地觀賞立體的雕塑。它提供給觀者的就只是多張不同角度的作品照片,觀者別無選擇只能在腦海主動成像,才能勉強形構出它的造形。
〈高雄市立美術館-數位典藏館〉
圖版來源:http://www.kmfa.gov.tw/desktop.aspx
相較之下,國美館大概是除了故宮以外最重視數位典藏的美術館,但它的數位典藏館卻不如我想像中數位化,或說是跟我認知的數位化有所差距。「迄今國美館已完成約2800件精緻典藏品數位化作業,後續研究結合多樣之數位典藏成品,進一步加值運用推廣,對於文化教育、衍生加值開發將是一個發展潛能無窮之文化資產寶庫。」[2]聽來國美館的數位資料庫相當豐富,但看到國美館在官網上刊載的數位典藏計劃的說明,再實際較對網上的數位典藏館之內容,裡頭居然只有二十六件立體作品有便於觀者瀏覽的三百六十度全景的互動介面,這是意謂整個數位典藏館只有二十六件立體作品嗎?絕對不是!只不過是不論媒材的差異,將這些以外的立體作品都以數位照片的方式來呈現、典藏。推算下來,國美館不就有兩千多件的作品都是運用數位攝影來進行數位化。根本的原因除了因為數位攝影是最適合平面作品的數位典藏技術,想而知裡頭應該大多為平面作品,如同官網上所說的數位典藏選件的其一原則-「容易呈現數位化成果」。[3]還可以為其辯解,肇因國美館一直以來的風格定位偏重現代台灣藝術,所以媒材交混或體積龐大的當代藝術當然較少典藏。話雖如此,我們也不能否認國美館的數位典藏在知識提供和互動設計上都確實不完整的事實。實際體驗下來,個人認為若是觀眾接收了這些不大人性化的數位典藏館所提供的藝術知識,奢望透過它們來清楚台灣當代藝術和陶藝的現況,想必只會糾纏不清!
〈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典藏館360度賞玩〉
圖版來源:http://www1.tmoa.gov.tw/collections/3D_View.asp
〈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典藏館〉
圖版來源:http://www1.ntmofa.gov.tw/collectionweb/01/index.html
不管是為了跟上e化的潮流,還是美術館間的競爭,或是在配合國家級文創計畫,筆者都認為現在該是放慢腳步,省思我們當前數位典藏機制是否有所缺失的時候。因為,由台灣官方美術館所主導的數位典藏館,其展現出的數位技術、互動設計與作品種類雖然都經典實在,卻也造就內容上的無趣和不夠完整正確。照理它們的館藏該是與故宮的水墨書畫、宗教雕像和古朝文物不同,但數位典藏的方法、結果居然大同小異。明明當代藝術並非全然古典,官方美術館庫房裡的藏品不致於應該調性一致,不過事實擺在眼前的螢幕上,台灣官方機構開設的每一間數位典藏館所賣的藥跟藥效明顯都差不多。它們都大量使用數位攝影拍攝平面(繪畫、攝影與影像處理)和立體(雕塑、裝置和陶藝)作品,掛上美術館官網就順勢代表了台灣的當代藝術。這是在告訴我們台灣沒有其他的當代藝術需要數位典藏?還是台灣的當代藝術其實沒有想像中多元?
不管如何,它們確實都間接彰顯了當前數位典藏所隱含的弊病!官方典藏的審查制度的確會連帶影響數位典藏的內容,評委極可能在挑選典藏標的時就優先排除媒材複雜、收藏不易和觀念取向的作品,原因不外乎典藏所需的硬體難以配合,要不就是不願屈就。不過,關鍵還是在於官方對於當代藝術的認知、喜好!畢竟要有機會成為數位典藏的選項,基本條件必須已是官方的藏品。而若繼續透過數位典藏館在網路散播,經時間積累發酵早晚會造成民眾認知學習到的藝術就是平面、立體與影像,是偏頗的藝術知識。到時別說期望縮小城鄉的文化差距,更不可能陶冶性情。因此,由官方意識所決定的結果若有失公允,觀者無法恣意欣賞作品就算,還可能接收到錯誤的知識。自我要求不高的台灣官方數位典藏的功能,對大眾來說只能作為圖檔與作品資料查詢之用。大多立體作品的數位典藏,只共置擺出幾張角度不同的照片就想表示出作品全貌,這若稱得上數位典藏,那大概不用期待這些美術館能建立出多貼心的數位典藏館。個人認為,理想的數位典藏不能只是為了提供民眾查詢資料而存在,還需負起讓觀者在任何地方單靠網路就能如臨現場般全面觀覽的責任。不能否認,不管它這是否是官方希望提供給民眾的典藏,它們還是有數位學習的用處,但我們都應對不夠完整的「它」持懷疑態度。再者,它們大多只以數位攝影來執行數位化,並沒有立基於作品媒材形式來開創數位技術與互動設計的其他可能。所以就算數位攝影所能容納的視界並非寬裕,但只要經過典藏與數位典藏的接連篩選,官方引以為傲的千萬畫素攝影、高解晰影像處理和攝影棚等配套完整的數位化技術與設備,理當堪稱足夠應付。可能也因官方認知的數位化技術就是數位攝影,沒有詳加考慮媒材與攝影的關係是否合宜,全以數位攝影來數位化藏品的機構亦大有人在。想來,無非攝影可是任何實物都能予以凝縮的技術。既然數位典藏免不了受典藏的選件與數位化技術左右其呈現,但若能促進開放的典藏與數位技術的交混,雖非全部也多少能讓台灣這些數位典藏館稍稍符合當代藝術的生態。身為e化時代的教育、推廣工具,它們「目前」的功能可沾不上教育,但數位典藏的「未來」可不能止於此。想當然未來收錄的作品只會更多樣,現在的「它」需要改變。
當真是數位複製當代的藝術作品?或只是技術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既然數位典藏存在的目的在於將藏品數位化典藏與數位化應用,反過來說,動搖官方美術館習用以久的數位典藏機制,機會也在數位!為了改變現行當代藝術數位典藏所潛在的內容失衡與形制單一,我們勢必要從「技術面」(數位化)切入分析數位典藏的現況,凸顯官方典藏機制與數位典藏之間的關係,正視我們正在使用的數位技術是否有所不足,召喚未來數位典藏的改變契機。
毋寧,台灣的官方美術館普遍使用於檔案化藏品的數位技術就是攝影!高解晰數位攝影、環景攝影,和多面向攝影的剪輯成像,頂多再加上針對錄像的拷貝與轉檔技術,不過幾種爾爾。想當然這些用途、效果皆異的數位化技術,適用對象(藝術品)也不同。高解晰數位攝影,無疑是每一典藏機構進行藏品數位化時必備的設備技術,幾乎任何具物理性質的作品都能凝縮成數位檔,連錄像都不免俗地會拍個幾張來建檔;目前最流行的無疑就是數位拍攝作品的各個面向再匯入剪輯軟體輸出成動態影片的技術,能夠呈現的不只是作品的單一面向,而是全面性的瀏覽,毋怪乎立體的作品往往要靠它才能在虛擬世界裡擁有體積;環景攝影,簡單來說就是由多台數位攝影機所共構而成,如此它才能環景拍攝。藉著它不止可以環景拍攝展覽空間的四面八方,還可以利用它輸出動態播放檔。想而知,與空間互動、結合的作品運用它就能如實記錄下場域!唯可惜器材昂貴,國內除數位藝術和房仲業,鮮少有機會應用於數位典藏;錄像或影片的數位典藏就單純多了,重點在作品母片的轉檔備份。雖然盡量保有原作影片畫質就夠,不過拷貝引發的智財權問題倒是錄像作品不同於他者的注意事項。乍聽之下,我們應當滿意當前台灣的數位典藏技術,但真要說來現行數位化藏品的技術過於依賴數位攝影,仍現代主義式地在追逐硬體的進步,迷思高解晰地再現作品「外觀」(appearance)。如此受限或說滿足於攝影器材的功能,久而久之官方機構會不自覺地認為數位化典藏就是將藏品轉換成數位影像檔,然後再建構出資料庫並在網路上架設數位典藏館就代表完成了數位典藏、活用了數位典藏。很自然地就遺忘數位典藏不只是在把藏品數位儲存和掛上網路,可還得盡力呈現原作的外表、真實反映藝術的世界才有意義。
反之,若數位典藏的對象不是傳統範疇的平面或立體作品,我們使用的數位化技術有能力在虛擬空間裡如實再現嗎?一定不容易,終究我們現在慣用的技術,並非針對各作品的形式而產出的數位化技術。正是由於不是所有作品都像平面(繪畫、攝影與影像處理)和立體(雕塑、裝置和陶藝)易於單憑數位攝影就完成數位典藏,台灣數位典藏的內容當然會不完整。當代還有許多交混著雕塑、裝置、繪畫甚至其他媒材所組成的作品,有些還是行動、互動的過程記錄與文件,它們往往因為沒有以數位攝影以外的技術予以應對,而無法登堂入室。需要解釋,這並非意謂筆者認為數位攝影不能用於這類作品,只是若希望盡量符合實物地在數位世界裡再現它們,就必須進化數位攝影這技術,甚至變革現有的數位化技術。一直以來,官方的數位典藏就缺乏針對作品形式來更新數位化技術與互動設計,沒有將作品形式、媒材設定為革新我們擁有的數位典藏技術之「變因」。改變是必要的過程,要不我們在網路上建構數位典藏館的意義將所剩無幾。雖然目前繪畫、攝影、影像和雕塑、裝置、陶藝仍是國內各大官方美術館數位典藏的主要典藏標的,現行的數位典藏技術還不致於會有改變的欲望與需求。但是,未來的數位典藏必然要不斷地擴增內容的豐富度,遲早會無法滿足於現有的數位化技術,到時自然會對開發數位典藏技術有所行動,當然也有可能會選擇繼續逃避下去!?於是,筆者認為當下必須結合、混用我們現行使用的數位化技術,才有可能更新甚至開創數位化藏品的技術功能。可以是機構上的混種結合也可以是透過軟體來混合應用現有數位畫技術的功能,雖然結果可能還是無法統包所有作品,但至少不致於讓數位典藏的內容繼續狹隘。
混雜(形式、內容)的當代藝術之於當代文化的混雜,隱約透露的連帶關係讓筆者直接聯想後殖民學者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所言的混雜(或稱交混,hybridity)概念。[4]「混雜」是霍米.巴巴自生物學引來詮釋文化後殖民的詞彙,它解釋了當代文化的交混與文化後殖民的影響,所以我們也不能否認後殖民造就的多元文化也同步影響著藝術的再現。藉此證明交混後的數位化技術,確實擁有拆解官方意識、開拓數位技術未來的潛在(virtual)。因為,「混雜性通常隱含著對權力關係之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否定與忽視。」[5]混雜的運作可以幫助我們忽視官方認定的主流與其他作品間的不平等關係,削弱內含於官方數位典藏裡的意識型態。需要強調,這由官方執行的數位典藏,官方意識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先天存在,它的存在無可避免!「混雜」就是官方澄清自己並非刻意施展意識的政治手段,同時逼迫數位典藏必須開放。換句話說,運作混雜的技術以中和數位化典藏含的官方意識的同時,其實是在正視這當代現象。正視當代藝術的多元差異,如同學者生安鋒所言:「巴巴質疑文化特徵描述中那些穩定的、自我統一的特性。他還聲稱,混雜性為積極挑戰當前流行的對於認同和差異的表述提供了方法。」[6]藉混雜的數位化技術,當代藝術在數位世界裡更能真實地表述它們(作品)的獨特與差異。此時就算官方主導的數位典藏命定內含主觀意識,「混雜」至少讓我們接收到稍加正確的藝術知識,縱然只是接近正確。
真要說來,根據現有技術進行的混雜實踐,本就是我們該做的基礎工程。所以光是靈活地交混應用數位化藝術品的技術,還不代表我們擁有足以數位典藏大部份當代作品的能力。「數位典藏」要真正名符其實地代表藝術世界,我們就不能忘記數位它真正的本事-「模擬」。[7]台灣正在進行或說它們所認知的數位典藏就是將作品予以數位攝影留存、應用,明顯遺忘還有借用數位軟體和程式工具在虛擬世界裡形構作品的造型肌裡這一招。台灣官方美術館使用於數位典藏的數位化技術,不過是憑恃著數位相機它那檔案化藝術品的機轉功能,連數位模擬的邊都沒碰到。引當代社會學者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在《象徵交易和死亡》(L’E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裡談到的擬像(simulacres)三類別(trois ordres)來解釋,台灣的數位典藏只能說是第二種,是「生產」(production)的擬像!我們的數位化藏品的技術不過就是依賴數位攝影來生產(複製)藝術品,可還沒進階到第三種擬像-「模擬」(simulation)。在今日,「模擬」早已在商業和工業領域裡應用到淋漓盡致,從立體實境的遊戲製作到產品、建築模型的構築,其軟體(MAYA、3D STUDIO MAX、PRO-E等)無不使用得相當廣泛平常。相對於數位典藏,大概除了故宮以外,少見官方美術機構運作程式軟體來掃瞄、輸入原作的外在規格,在數位世界「演算繪製」(render)出翻版的原作來數位典藏。所以,布希亞關於數位時代「模擬」擬像的概念並不合於詮釋台灣數位典藏的技術,反倒是它工業時代「生產」擬像這的概念源頭,也就班雅明在一九三六年發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裡談及的技術複製藝術品的思考更為貼切我們目前數位化藏品的技術。說明白,台灣目前數位化藝術品的技術徒具硬體先進,技術仍停留在工業時代的複製生產,還是在生產藝術品的擬像,跟過去一百年來相機還沒有數位化的技術複製藝術品的方式一樣,差在承載影像的「容器」(檔案與相紙)不同罷!
「到了二十世紀,複製技術已達到如此的水平,從此不但能夠運用在一切舊有的藝術作品之上,以極為深入的方式改造其影響模式,而且這些複製本身也以全新的藝術形式出現而引起注目。」[8]我們現在使用的是數位化藏品技術就是藉數位攝影迅速地產出高解晰的作品影像,這是我們數位典藏的水平!?聽來還算先進,但要知曉來到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快結束的現在,數位相機的「生產」只是其一數位化藝術品的方法。而數位從零到有的「模擬」本事,則從未發揮!其中3D繪圖軟體可是擁有其他數位技術難以企及的建模,以及足以仿原作般真實的Bump-Mapping(中譯:凹凸貼圖)功能。於是,「模擬」處理許多難以依恃數位攝影完整呈現原作樣貌的作品,讓它們得到比原作更接近原作的真實!,
筆者認為現行官方美術館呈現給我們社會大眾的數位內容固然數位化,卻非完全體的數位典藏,所以才會造就現實生活裡的數位典藏與個人認知有所差異。不管是台灣官方美術館不習慣使用軟體來執行藝術品的數位化,還是它們根本懶得學習這些軟體,才不得不執著於硬體設備的數位功能!?都可以確定我們再怎樣活用數位攝影,數位化藏品的技術絕對不夠,所以需要交混更新現有的方法。但,相對於當代藝術的多樣,數位化藏品的方法仍顯不足。不過若再加上數位的模擬,情況可就不同。至此好歹清楚了一些狀況,首先,透過交混也就不至於受限於硬體的設備,放大我們數位典藏的範圍標準;況且今日數位科技的發展早已臻至只要有原作,甚至影像資料就可以進行「物」的模擬,但當前台灣卻尚未應用程式和軟體來著手藝術品的虛擬建模和3D模擬,致使錯失數位典藏許多作品的機會。因此,培養、招募電腦繪圖人才進入數位典藏的領域實乃時勢所趨;再說,就算我們兼具合用的硬體與合宜的軟體亦不見得就能真實地數位再現。我們還需要建立一套套從硬體接續到軟體,一貫數位化藏品的工作模組。這不同於數位攝影機和繪圖剪輯軟體有現成的可供取用,接合硬體機能與軟體功能的作業模組要靠我們自己官方美術館主動去開發。唯有如此,待積累了足夠的作業模組與數位經驗,方能不受數位化藏品的工具束縛我們數位典藏的內容呈現,恣意地運作技術生產與數位模擬。
數位典藏的當代性,數位化的當代藝術
無庸置疑在數位典藏上,我們辜負了數位。需要澄清的,這不表示數位攝影就相當適用在平面和部份的立體作品上,只不過是證明使用數位攝影來進行數位化確實不至於失真。但吾認為針對平面(繪畫、攝影與影像處理)和立體(雕塑、裝置和陶藝)的數位化技術雖然實用卻不見得是最好的,這在具象繪畫的數位再現上就能驗證。許多具象繪畫裡其中可還有物與物、物與空間、人與物、人與空間以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存在,然而數位攝影雖然可以如實地複製畫中世界,卻不能解構畫裡頭的一切關係,幫助觀者理解這幅畫的結構與敘事。像筆者2008年於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觀賞丹麥畫家Vilhelm Hammershøi,Interior(1964-1916)靜謐的詩情(The Poetry of Silence)個展現場所看到的數位典藏與再現的模式,就是運用了3D的建模,建構出Hammershøi畫中的世界,甚至藉著多張比對在虛擬世界建構出作者所設定的空間格局。需要知曉Hammershøi作品裡的空間並不一定完全跟現實空間一樣,藝術家經常為製作空間與官感上的效果而在畫中變換或說任意組織這空間的格局,因此也唯有利用多維的重建,才能讓我們清楚藝術家畫中的空間,甚至畫中人跟她所處的這個空間的關係。
Hammershøi,Interior, 1908
圖版來源:http://www.guardian.co.uk/artanddesign/gallery/2008/jun/25/art.denmark?picture=335262248
參照2008年台北雙年展,作品全然不是傳統認知的油畫和雕塑,展覽以錄像、複合裝置、社會行動和觀念藝術為主,大多無法成為官方典藏的選項。尤海.阿弗拉哈米(Yochai Avrahami,1970)的作品〈前有暗礁〉(Rocks Ahead)就是往往會不受青睞典藏的範例,無非因為它是由雕塑、裝置與錄像所形構而成的單一作品,就算使用全景攝影拍攝,觀者目光移至錄像時豈不只看到定格的畫面而非動態影像。顯然我們需要混合的數位化技術方能解決,讓觀者在網路上毋須受制於需要分開觀看一件多媒材作品的各部份,我們可以瀏覽作品的圖像亦同步看這作品它的影片。或許可以專為這類作品書寫程式,讓觀者在全景瀏覽時還可以點選影片來放大播放的互動技術。當然,要應付這多元的當代,軟體還要配合硬體不斷地更新,才可以讓數位典藏不受作品的形式風格所局限。此外或許有人會提問,當代藝術許多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就是企圖反對美術館機制,我倒認為典藏跟作品意圖是兩碼事,不能說明我們不需要持續創造數位化藝術的作業模組。再說,很多作品觀者皆無法親堵它的完成,但藝術過程中留下的影片與文件其實都是可典藏的,數位技術就可以拼組出相較於觀者在美術館看到的記錄文件來的接近作品的真實,數位它有機會辦到!丘旼子(Minja Gu,1977)在北美館建築館體上製作的〈秘密花園〉(Secret Garden),雖有實體卻擺脫不了展覽過後的拆除命運,它無法典藏;吳瑪悧,〈台北明天還是一個湖〉,現地製作、裝置,2008
圖版來源:個人拍攝
湯皇珍,〈我去旅行V(威尼斯雙年展)〉,2007
圖版來源: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回溯藝術史來清楚當代多元發展的端倪,早自達達主義(DaDa)、國際情境主義(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福魯克薩斯(Fluxus)至偶發藝術(Happenings)的創作手法,再再讓人(觀者、參與者)與藝術的關係不停地抖動變化著,造就爾後的地景藝術、觀念藝術、錄像裝置、數位互動、社會藝術和文化行動主義等,甚至還有許多其他類別的藝術,只要關乎非單一媒介與人為介入,官方機構皆不易典藏,更遑論進入到數位典藏的程序。這現象彰顯兩點我們必須打破的迷思,首先典藏不是只為收藏完整作品而存在,作品的過程文件也可以典藏;另外,只要開發出交混的數位化技術和數位模擬的程式軟體,也就不一定需要完整的作品典藏,亦可能毋須在典藏時排除媒材與形式繁雜的作品。數位的潛力可還沒完全發揮出來,它可以交混(混種)多種數位技術的實踐數位化典藏,或者單靠資料匯入電腦用軟體和程式運算也行。想來也真的有太多作品我們無緣親至美術館見它一面,有時還根本不可能見到它的「完成體」,所以我們發明了數位典藏。數位典藏的方法學建構是官方和私人的典藏單位都要面對的課題。專門的數位化技術才夠資格將藝術不失本色地在網路上再現,畢竟典藏機構可還要負起正確的藝術教育與推廣責任。
數位典藏的詮釋與再現,政治工具的責任與功能:淪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透過實際地操作與瀏覽這些數位典藏館提供的「服務」,歸納當前的數位典藏之所以與事實的藝術世界脫勾,無非就是肇因於台灣官方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內容仍舊以平面(繪畫、攝影與影像處理)和立體(雕塑、裝置和陶藝)為主要數位化的標的,加上數位化藏品的技術耽溺於硬體功能的進階,根本上忽略硬體的多元應用與程式(軟體)的研發。數位典藏的目的不止是為留存原作樣貌與資訊而存在,更重要是依恃網路媒體的普及、快速,提供觀者連上數位典藏館來學習與認識藝術。好說光憑上述就可以讓觀者透過寬頻網路連線至典藏機構的數位典藏館,即時點閱欣賞感興趣的作品。試想,民眾身處任何地方,只需台內建網路卡的電腦就可隨意識來點閱作品,接受藝術陶冶不需要親身前往美術館、博物院。網路,讓藝術更平易近人之餘,進而向世界宣揚自身擁有的文化資源。推廣藝術的方式改變已然應驗了法蘭克福學派學者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84)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所言:「機械複製可以將複製品傳送到原作可能永遠到不了的地方。」[9]數位典藏想當然成為藝文推廣的必要工具,單憑手指的點擊,從平面ZOOM-IN、ZOOM-OUT到三百六十度的全景翻轉,更甚還能複合地立體翻轉又放大、縮小來閱覽。網路如此地便捷,就這麼發揮了它身為官方政治工具的效果-藝術教育!需強調,藝術典藏身為政治工具並無不好,反而代表它能力強大,責任也就愈重。評斷一個數位典藏館的優劣依據,在於它是否能提供正確我們的藝術知識,發揮它應有的功能。
總的看來,不論從數位典藏的機制面還是技術面看來,大部份官方美術館的數位典藏館,藉網路向觀者推廣與教育的藝術知識,只是「介紹」這多元當代的抬面上部分。縱然數位化的作品是普遍認知的主流,但觀眾學習到的卻是失真的知識,這是官方的希望嗎?不將作品當作數位典藏的核心,反倒受制或說滿足於數位典藏技術的先天功能,忽略創新。轉向思考,官方不正是缺少典藏選件所需要的開放態度!它們希望作品易於典藏入庫,數位典藏就可單以基本的數位技術來處理,也就毋需進行數位化技術的開發,導致官方往往以方便典藏和媒材傳統的作品為標的,便於內部典藏與數位典藏,著實可以理解官方的用心良苦!
官方的用心或許還不止如此,它們運作數位複製讓藝術品不再具儀式性,消除了藝術品的「靈光」(aura)可還別有用意。「藝術從傳統中解放,不再依賴儀節和原創性(Originality)來塑造神聖的想像,藝術服務的對象(觀眾)擴大,展出的機會變多,也更便於展演,展演價值給作品帶來全新的功能。」[10]數位典藏不就是為成全藝術教育和文化推廣功能而存在的工具。它隱而未顯,卻實實在在表明官方認知的藝術,官方的數位典藏免不了成為政治工具!相對而言的前題,數位典藏身為政治工具有責任要用得好、用得正確。據Anne D'Alleva撰“Methods & Theories of Art History ”,裡頭就談到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對意識型態的看法,說道資本社會的永續是靠著兩種手段,一是如刑罰、警察和軍隊等壓制型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RSAs)的指導與壓制,另一就是運作教育、宗教、家庭、媒體和文化等來掌控民眾,即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ISAs)。[11]當前台灣數位典藏所提供的知識不就有如後者,是政府灌輸正確的藝術認知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數位典藏館有如日據時期的學校,透過老師(網路)進行皇民化教育,潛移默化「正確」的國家意識型態。值得注意,官方典藏與數位典藏稍不小心將陷入國家意識型態的窠臼,網路就是操作意識型態的場域,民眾在線上典藏館吸收學習到的藝術知識,不過是一次次地承受文化霸權(hegemony)。[12]
如此言重卻只單憑現況的了解而沒有量化調查,的確不當。但是,「『顯明性』-視為理所當然-是意識型態運行方式的重要特徵。」[13]當前台灣民眾所認知的當代藝術,仍舊理所當然會認為就是繪畫、雕塑和陶藝。稍感欣慰李安、蔡明亮的影響,喚起社會對於藝術電影的關注,那其他類呢?數位典藏發展至今,我們不得不重視數位典藏對社會以及未來的影響!當前數位典藏的內容如此,不能否認其中有受到官方典藏的策略選件與缺乏數位技術、互動規劃所間接影響,是典藏與數位典藏的技術性共謀!「技術性」意指兩層面,一是典藏機構透過技術性(官方機制考量)選件以利典藏入庫和數位典藏;二方面就是數位化技術的考量,官方受制或說滿足於現有的數位化技術,於此同時也桎梏了可以進行數位典藏的作品選項。筆者就只從數位典藏表面上的成果看來,毋論官方是有心或刻意,內容確實可詮釋為政治的意圖,即使官方機構當真只是為避免麻煩而決定的選件,或是技術上受限而有所偏頗的數位典藏,它們所再現出的台灣當代藝術,卻可能讓身為政治工具的數位典藏,無法開脫淪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罪名!
[1] 華特‧班雅明 著/許綺玲 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68頁,台北,台灣攝影,民87。
[2] 節錄自:國立台灣美數館官方網站
[3] 節錄自:國立台灣美數館官方網站
[4] 註:十七世紀時,「交混」這個詞語所指涉的是,不同「種」的植物與動物交配之後所產生的新品種,在目前的跨文化研究與後殖民研究當中,「交混」則是十分重要且使用頻繁的詞彙,因此「交混」不但可以去除制式的想像和疆界,在交混雜糅的曖昧地帶間,更可以提供各種多元想像與抗拒力道的發聲空間。廖炳惠 編著:《關鍵詞200》,133頁,台北,麥田,民92。
[5] 生安鋒 著:《當代大師系列─霍米巴巴》,192頁,台北,生智,民94。
[6] 同上,148頁。
[7] 註:這個詞源自希臘哲學,在一般用法〔譯按:這種用法常譯為「模擬」〕裡,經常是指電腦的程式化與模型製作。在當代文化理論裡,最著稱的是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的用法,指涉影像與其真實生活指涉物之間生變的關係,或說是以布西亞的結構主義語彙來說,符徵與符旨之間關係的變化。
[8]華特•班雅明 著/許綺玲 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61頁,台北,台灣攝影,民87。
[9]華特‧班雅明 著/許綺玲 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63頁,台北,台灣攝影,民87。
[10] 白婷尹 撰:《班雅明美學在台灣作為一種防衛機制》,20頁,民96,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論文。
[11] D Alleva A. ,Methods & Theories of Art History ,Laurence King ,p.51,London.
[12] 註: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他的《獄中書簡》(Prison Letters)中提出這個概念,主張支配階級往往會透過非武力和政治的手法,藉由家庭、教育、教會、媒體與種種社會文化機制,形成市民共識,使全民願意接受既有被宰制的現況。「霸權」在這樣的意義下,儼然是社會文化規範和標準的推動者,它不只是一種柔性的說服手段而已,更經常透過複製統治階層所彰顯的社會利益,來使統治的威權暴力合法化和正當化。因此,「霸權」是深刻織縫在日常生活紋理當中的,透過教育和宣傳,它不只是會使人們在意識型態的呼籲和召喚(interpellation)中,把許多主流文化的假定、信仰和態度視為理所當然,它也同時超越於所謂的政治經濟體制(如國家或市場)之外,在常民生活中形成微妙且無所不包的力量。廖炳惠 編著:《關鍵詞200》,130頁,台北,麥田,民92。
[13] John Lechte 著╱王志弘 劉亞蘭 郭貞伶 譯:《當代五十大師》,73頁,台北,巨流,民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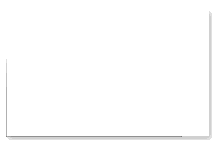





四月 30th, 2009 at 2:54 下午
覺得作者所陳述的是很多面向的問題,卻混在一起探討。
第一,什麼藏品適合進入美術館,這是各館的收藏政策。的確有作者所說的官方意識存在。但前提是要先成為美術館典藏品,才會由單位進行數位化。
第二,美術館進行數位典藏,重點是’典藏’,經費上不一定足夠,當然會有選件。以最重要的平面或三D者藏品先進行也不為過。
第三,官方網頁上開放出來,不代表是所有數位化的成果,各館有各自的開放政策。若以此,進行評斷哪各館做的好或不好,恐有失當處。特別是當代藝術,有很多智財權的問題,無發直接放在網路上讓全民瀏覽檢索。
第四,數位典藏,是以典藏為最主要目的。作者所說的以多元的方式進行數位化或呈現,我覺得這是’數位典藏’後的下一步’數位加值’或’數位學習’,要努力的方向。
第五,此時,在’數位加值”數位展示”數位學習’等方向上,才是作者所述,在現代藝術上的努力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