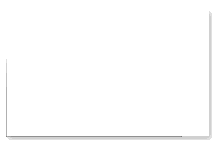《中國時報》新聞攝影底片之數位化-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裡的政府與政黨新聞,1988-2000
文/鐘宜杰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因而解除黨禁與報禁;解除戒嚴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台灣人民因而獲得言論與集會遊行的自由。其中報禁的解除,促使許多民間人士投入辦報事業,讓台灣的報業市場從過去黨國箝制與國家干預的環境逐步走入市場的自由競爭環境。解嚴前舊有的幾家報社,諸如《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以及後來結束發行的《自立晚報》、《自立早報》等,均在報禁解除後同時面臨市場競爭與資訊科技進步的挑戰與壓力。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因而解除黨禁與報禁;解除戒嚴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台灣人民因而獲得言論與集會遊行的自由。其中報禁的解除,促使許多民間人士投入辦報事業,讓台灣的報業市場從過去黨國箝制與國家干預的環境逐步走入市場的自由競爭環境。解嚴前舊有的幾家報社,諸如《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以及後來結束發行的《自立晚報》、《自立早報》等,均在報禁解除後同時面臨市場競爭與資訊科技進步的挑戰與壓力。
市場競爭與資訊科技進步可以看成是兩個問題,但是兩者卻也息息相關;因為資訊科技影響生產模式與生產關係,所以也關係傳播產業的生產成本及生產效率。解嚴以後的資訊生產,受到網際網路的普遍化影響甚鉅。1994年日本廣島亞運,台灣攝影記者除了使用古老的美製滾筒式底片掃描傳真機(leafax)之外,同時也使用撥接式數據機,以Email或FTP傳輸技術將新聞照片從日本傳送回台灣。彼時,還只能算是半數位時代,攝影記者仍然以底片拍攝,再將沖洗完成的負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傳送(滾筒式掃描傳真機則是用類比方式傳回四色底稿)。時至1999年底,九二一地震後,台灣主要報社多半已經全面使用單眼數位相機了。爾後,攝影記者的隨身配備多了一台筆記型電腦與各種傳輸設備。今天,十年的光景,數位攝影已經普及到人人皆可攝影,處處都是數位影像。若說1888年柯達公司推出價格低廉、操作簡單、使用乾式底片的輕便式相機,讓攝影走入家庭,是攝影史當中一個重要的技術解放,那麼二十一世紀初數位攝影的發展,便是繼1888年之後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
因為攝影技術的普及化與通訊技術的進步,讓今天資訊傳遞的速度遠比二十世紀快速許多,也不再是掌握在少數專家手中的特殊技術。一個國小學生,只要手中持有照相手機,便可以將眼前的事物拍攝下來,即時傳送到地球上任何通訊可達的角落。打開網路相簿或部落格,我們可以看到億萬張的照片張貼在網路空間裡;照片出現在今天的資訊環境中,已經顯得極為簡單與理所當然。然而,正因為照片在現代化的社會生活是如此容易取得,便能與二十世紀末期的底片攝影形成對照,突顯出底片攝影時代的差異性與其珍貴價值。
採取較感性的描述方式,我們可以說,底片影像是有生命的。一張被拍攝下來的影像,經過沖洗、放大,無論是底片還是照片,從定影完成後便開始老化,總有一天會死亡(氧化至損壞殆盡)。許多專業攝影師絞盡腦汁想要延長底片的壽命,但也僅是延長,而非長生不老。一張照片是不是一定要長生不老?這是另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但現在我們所討論的,以及攝影數位化的科技發展,則是一個讓影像能夠永久保存的企圖。
戒嚴與解嚴時期的新聞攝影照片的今日意義
戒嚴時期,人民不僅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資訊更是受控於少數菁英與掌權者手中。在黨國一體的政治環境中,傳播媒體傳遞的多半是歌功頌德的正面消息;報紙上的新聞照片既少又小,呈現的內容不是安排拍攝的官式照片,就是觀點與視角一元化的紀實拍攝。
一九八○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黃金時期,為不滿於當時政治與社會環境的知識分子展開了無限的發展空間,眾多有志青年投入報導攝影行列,包含《中國時報》在內的許多報社也在此刻召募了大批的攝影新血。這些熱血青年投身媒體、走入群眾原鄉、貼近底層社會、記錄人間故事。他們懷抱著人道主義,勇敢地說出事實真相,讓許多因為城鄉差距與資訊不對稱所不為人知的故事,在這段時間因而有機會在媒體上被揭露。
與戒嚴時期相對照,一九八○年代所生產出來的大量寫實影像,自有其歷史意義與重要性。這些照片記錄台灣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讓沒有參與歷史的人可以藉著這些照片了解當年所謂「老國代」指的是哪些人、五二○農民大遊行的激烈狀況、少數民族與弱勢族群如何爭取平等、冷戰結束與柏林圍牆倒塌以後台灣跟著產生了什麼改變、解禁以後的飆車族如何在社會中出現、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台灣青年知識分子做了什麼事、萬年國會如何走入歷史…等重要的歷史與社會事件。
《中國時報》攝影部門發展簡史
《中國時報》自早年的《徵信新聞》時期成立了攝影部門,1960年改名《中國時報》後,擴大了攝影部門的編制,招募了許多知識分子擔任攝影記者。已故的余紀忠先生在台灣報業間素有愛才惜才的雅譽,與今日資本家經營媒體的僱傭勞動關係有顯著的差異,《中國時報》攝影組因此匯聚了許多攝影菁英,分佈在報系中的《中國時報》、《中時晚報》、《工商時報》,以及《時報周刊》。
伴隨報禁解除的市場競爭及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傳播革命,台灣主要報紙均如臨大敵地面對這場難以避免的割喉戰。《中國時報》自1987年以後便不斷地調整組織結構、人事布局,以及進行硬體設備的更新,其中包含攝影部門如何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將新聞現場的影像送到編輯台。為此,《中國時報》是國內第一也是唯一自行購買底片沖洗設備的報社,也就是攝影記者拍攝的底片不必送到沖洗店排隊沖洗,直接回到報社用自家的快速沖洗機沖洗出底片,再經過高階掃描後傳送到編輯台。這樣的投資,不僅大幅減少了攝影記者舟車往返與排隊等候沖洗的時間、提高了發稿效率,同時也有效控管了快速沖洗機的藥水品質、減少底片受損的機率與延長底片壽命。
1999年《中國時報》成立「聯合攝影中心」,統一調度《中國時報》與《中時晚報》兩組攝影記者。隨後又將「聯合攝影中心」改制為「影像中心」,將報系下的《工商時報》也納入調度範圍。如此的整併工作有利於編輯部管理攝影部門的人員與照片,減少不必要的人力浪費。舉例而言,過去往往一個新聞現場同時出現了《中國時報》、《中時晚報》、《工商時報》三組攝影記者,各自攝得的照片同質性極高;整併以後,影像中心主任則可以視情況需要而派遣適當人數到新聞現場,有效掌握當日所有的新聞照片,不論對於發稿或是匯入資料中心建檔,均能減少不必要的人力與財物虛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中國時報》出版了《台灣˙戰後五十年》圖文書。這是一本以圖片為主的編年史錄,記錄了自1945年到1995年間台灣所發生的政治、社會、人文大事;《中國時報》當時對影像的重視,可見一斑。然而時至今日,報業市場萎縮、市場結構改變,以及該報經歷改朝換代與不敵市場競爭而易主的殘酷事實,商人辦報取代了文人辦報。報紙成為眾多資訊商品中的弱勢商品,作為一種資訊商品,攝影部門儼然成為報系的圖片供應生產線;所生產的圖片不再是攝影記者獨到與敏銳的觀察,以及富創意且深具意涵的優質影像,而是追隨市場取向、人云亦云的聳動畫面。《台灣˙戰後五十年》已成絕響,攝影文人退場,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接單赴任的攝影工人。
《中國時報》便是前述完整經過底片攝影時代、半數位化時代,以及全面數位化時代的國內主要報社之一。作為一個社會重要的新聞資訊來源,《中國時報》將歷史新聞底片予以數位化自然有其正面的意義。尤其,將歷史影像數位化並有限度開放成為一定程度的公共財,更具有資訊解放的實質意涵。以往我們要進行歷史研究,總是要奔走於圖書館、國史館,以及各個民間組織之中,才能瀏覽到罕見的歷史圖片。若能取得同意進行複製,頂多也只能以相機翻攝或者影印保存。這些複製效果多半僅能達到「可辨識」的程度,很難獲得清晰的影像,讓研究者與閱眾僅能靠想像來填補失真的影像空缺。這些歷史影像的原稿若能夠透過數位化建檔分類,對於學術研究必然是一項珍貴的資源。
歷史影像數位化的意義與幫助
台灣的報社向來沒有重視影像資料的觀念,包含擁有大量影像資料庫的中央通訊社在內,始終沒有有效地管理影像庫。直至網際網路普遍化,以及港媒《蘋果日報》登台發行以後,影像逐漸成為這些媒體重要的資訊媒介,台灣媒體才在市場競爭中覺醒,開始重視影像庫的管理與利用。以《中國時報》而言,早期建檔的數位化圖片皆是經過記者挑選而發稿的新聞照片;這些為了符合當日新聞需要而被挑選的照片,其影像的意義有其侷限性。換言之,不符合當日新聞需要的影像便被閒置在底片庫當中,而這些底片也會隨著時間逐漸老化,最終損壞至無法使用。
今日,《中國時報》欲將1988年至2000年間的政治新聞照片數位化建檔,並提供給學術單位使用,是媒體作為一個社會公器應盡的責任,也是一項具有遠見的計畫,為時雖晚,但值得與時間追趕。不僅如此,更建議該報逐步擴大建檔類別與年代;不只是政治新聞,還要擴大至各版各類的圖片,並追溯至所有尚能使用的底片所屬年代。此外,許多僅留下「紙本照片」的檔案,也應該以高階平台式掃描的方式加以數位化保存。
歷史影像經過數位化而成為一定程度的公共財,是資訊民主化的重要步伐。解除戒嚴對台灣人民而言是政治民主化、言論鬆綁、資訊自由的象徵,然而媒體商業化卻也讓新聞自由掌握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國家機器雖然解除了對人民的言論箝制,卻將新聞與言論自由的權利交付給另一個宰制性更強的權力結構。這個權力結構將意識形態透過更微妙、更隱晦的方式潛藏在資訊產品之中,使閱聽眾不知不覺地屈從其下。其中,資訊與媒體近用權的壟斷即是其與民主精神悖逆的主要之處。
今日的《中國時報》已經是個完全由商業集團經營的媒體,姑且不論其政治立場與商業利益考量,報社作為一社會公器,能夠與政府及學術部門合作,將部分的歷史影像予以永久保存並成為公共財,就事論事,是能夠予以肯定的作為。我們希望這是一個拋磚引玉的舉動,讓更多媒體集團能夠投入這項工程,為台灣歷史盡一份力量。
於後的省思
歷史影像經過數位典藏而能獲得永久保存的機會,固然對學術研究與資訊公共化有一定程度的意義。然而除此之外,尚有一些重要且長期被忽略的問題需要加以正視。
長久以來,攝影記者在台灣始終是被忽略的一群,許多珍貴、深具意義、震驚人心的照片,人們總是記得影像卻不記得出自誰手。在台灣的新聞職業場域中,攝影記者向來僅是配角;在職業關係中是如此,在新聞版面中也是如此。如今,攝影記者更是新聞場域中的影像快遞、攝影苦勞。我們該如何保障這些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並提升其專業性?是新聞傳播研究必須重視的課題。
此外我們注意到,這些新聞照片的「所有權」是屬於報社,而非拍攝者;攝影記者與報社簽下著作權轉讓,在台灣是長久且普遍的慣例。換言之,攝影記者在工作中所產製的所有圖像,攝影記者自身都沒有權力作為他用。生產者與其生產物之間產生了異己關係,其中代表了什麼意義,已經不必贅述。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能讓這些影像工作者繼續保持高度的熱忱並維持其專業性,顯然與期待有所扞格。因此,「所有權」亦是未來必須考量的問題。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國家正積極地進行數位典藏與永久保存,但這項重要的工程在攝影記者之間卻相對地不是那麼積極。主要原因除了「所有權」問題讓記者處理上顯得尷尬之外,所需要耗費的時間與工程費用也非常高。要付出這樣高的代價,往往就會思索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市場」在哪裡?台灣缺乏制度化與規模化的攝影市場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也影響了整個攝影文化的發展。如果台灣早有健全且成熟的攝影市場與文化發展,那麼今天將歷史照片加以數位化典藏的機構可能不會是由國家主導、由納稅人付費,而是由市場與文化機制內主動完成。國家力所做的,頂多只是收購並予以公共化罷了。
上述的三個問題,突顯了國內長期忽視影像文化的現象,也是個人認為媒體改革過程中,關於影像部分務必正視的問題。時間會繼續流動、歷史會繼續累積,期待再過五十年,我們的後代有珍貴的歷史影像可以參考,也有豐富的影像文化研究成果,但不必再有這些困擾。
延伸閱讀:
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中國時報》新聞攝影底片之數位化—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裡的政府與政黨新聞1988-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