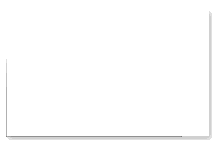追蹤文化匯流的足跡:從佛典詞彙的演變談起
當你遇到不會讀的字時怎麼辦?我想多數的人第一直覺就是查字典,我們可以用部首查到字,再從注音符號瞭解字的讀音,甚至進一步瞭解它的意思,更方便的,還可以透過線上國語字典來查詢。但是古人又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呢?我們現在習慣使用的注音符號,其實是1918年才開始正式推行使用,在這之前,並沒有注音符號告訴我們怎麼讀難懂的字,那時候的人們如何克服這個問題?
在早期,我們的老祖先其實是用簡單的字之讀音,去解釋難讀的字音,例如在《說文解字》這本東漢最著名的字典裡,他解釋「卸」這個字的讀音時,便說「讀若汝南人之寫的寫」,是用「寫」來模擬「卸」的讀音,不過若遇到較複雜的情況,便很難直接以一個字來解釋另一個字的讀音,因此產生了「反切法」的方式。所謂「反切」,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拼音,是使用兩個漢字來拼讀出一個字的方式,也就是用前一個字的聲母、後一個字的韻母拼出一個新的音讀。例如《廣韻》:「東,德紅切。」便是指「東」字的讀音,是由「德」字的聲母以及「紅」字的韻母所組成。這種「反切法」的產生,一方面與漢語本身的發展有關,另一方面則來自佛教的影響。
佛教能盛行於中國,與佛經的翻譯有很大的關聯。為了能將教義傳達給更多的人,或是擴散到更廣的區域,往往必須藉由書面的記載與傳播,但是佛經翻譯之初,通常是透過來自西域的高僧進行口誦,再由漢人記錄下來,來自西域的高僧並不熟悉漢語,而記錄的漢人也不一定瞭解梵語,所以早期佛經的翻譯並不準確,產生許多翻譯方法的問題與爭辯。就在這爭辯與翻譯梵語的過程中,翻譯理論及方法逐漸成熟,同時受到梵語拼讀特性的啟發,漸發展出獨特的「反切法」。
此外,佛經中有許多概念是中國所沒有的,那又該如何進行翻譯呢?每個譯者處理方法不同,有些人可能省略不翻,或直接套用中國既有、相似的概念,甚至只翻譯聲音、創造新的詞彙,這種種紛雜狀況都使佛經中的詞彙產生相當多的歧義。這些歧異不只困擾現代人,也困擾著我們的老祖先,針對佛經閱讀而編撰的辭書因應而生,現存最早的佛學辭書便是《玄應一切經音義》。
史料中並沒有記載玄應的生平,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其他文獻中得知,玄應曾經參與玄奘譯經場的翻譯工作,所以有機會蒐集佛經中各式難讀、難解的詞彙,並以反切的方法解釋其音讀,不只如此,還引用許多當時其他辭書或典籍中的註釋。我們不難想像,玄應在解釋佛經的詞彙時,一定是選用當時人們所能理解或是熟知的詞彙,甚至是口語化的語言,這樣辭書才有著「解釋」的功能,但從現在的語言習慣看來,依然存在著理解上的巨大隔閡,然而,這正是語言衍化必然產生的狀況。
語言處在不斷變化當中,當周遭環境改變,所多事物或觀念隨時間消失了,這些串連著觀念與實物間的詞彙,也會逐漸被人們遺忘。另一方面,若是出現新的事物或概念,勢必也會出現新的詞彙,用以承載這些新的意涵,所以詞彙的增加或是詞義的更新演進,皆與社會文化的發展緊密相依。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因為受到外來語言的影響,這樣的現象尤為明顯。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想,這些造成理解障礙的擾人詞彙,其實記載著中國文化在不同朝代、地域發展的足跡,我們不妨隨著這些看似陌生難解的字句,去領略語言與文化之間的交融與匯流。
要體現語言與文化的交會和差異,可以從「野狐」這個有趣的詞彙看起。我們看到這個詞彙,最容易聯想到的,應該就是在林野間奔竄的小狐狸吧,在佛典中,也常用野狐來作比喻,例如北梁曇無讖所譯《悲華經》便有「或見似象、或似野狐,在佛前坐,聽受妙法,隨時思惟,各自見身如是相貌。」另外在求那跋陀羅譯的《雜阿含經》還有一個故事:「彼野狐者。疥瘡所困。是故鳴喚。若能有人為彼野狐治疥瘡者。野狐必當知恩報恩。」野狐在此二經中,被用來比喻為會報恩者。不過,這與中國社會的認知大異其趣,以《說文解字》解釋「狐」為例:「獸也,鬼所乘之」,由此可見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狐並不是會知恩圖報的善良小動物,而是一種妖獸,專門供鬼騎乘。另外在《太平廣記》中也收錄有狐的靈異故事,如其中一則〈說狐〉:「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盅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這樣的觀念,其實與我們現在口語中的「狐狸精」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隨著時代演進,佛典中的野狐所表徵的形象,也受中國社會的觀念影響而改變,如唐代阿地瞿多譯《佛說陀羅尼集經》時,便有「若鬼神變形,或作大蟲及野狐等種種諸身,入人身中令其病者,當作此印誦咒即差。」佛典中的野狐似乎已有神鬼化的傾向,並代表某種不知名的邪物。而這在中國僧人著述中更為明顯,例如禪宗的《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語錄》:「真佛無形真法無相,爾秖麼幻化上頭作模作樣,設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真佛,是外道見解。」在此比喻中,野狐能變幻為人或變形為其他樣貌,用以欺瞞他人,所以對於一些未開悟而自稱見性悟道的人,便稱呼其為野狐精或野狐禪(野狐禪為另一禪宗著名公案)。明代《四分律名義標釋》:「狐,洪孤切,音乎。形類黃狗,尾大鼻尖,心多疑,能善聽。謂其性多疑,每渡河冰,且聽且渡,故今言疑者,而稱狐疑,又云,北風勁河冰合,要須狐行。此物善聽,冰下無聲,然後過河。其性多淫,老狐能為妖魅迷人,謂千歲能變為婬婦,百歲能化為美人。」便是把狐的動物性與靈異性結合,並將前述幾本典籍中的野狐形象做綜合的整束。
野狐這個例子分析起來有幾分趣味,但是要作這樣的資料收集,可能要費一番功夫,甚至要把所有佛典讀過,耙梳相關詞彙的脈絡,分析整理各詞彙出現的時間順序和地點,接著再查閱當時的辭書以瞭解詞義的演變。似乎要花上十年光陰才有辦法完成這樣的研究,但現在,有了數位技術的幫助,只要輸入「野狐」這個詞彙,以上所有的工作,電腦都可以幫我們做好!這樣便利而且有效率的系統建置完成,除了歸功於數位技術和網際網路的進步之外,也全賴法鼓佛教學院這多年來的努力。
法鼓佛教學院執行佛典數位化工作已有多年的經驗,在過去的成果積累上,提出了「整合性佛學資料庫」(Integrated Buddhist Archives, 簡稱 IBA)概念,希望整合現有以及未來的佛教文獻數位資源,有許多相關的專案,都正朝這共同目標而持續的進行著,其中「台北版電子佛典集成之研究與建構」計畫,即是著重在佛典文獻的數位化,這對於佛典文獻的傳播或後續的研究,提供了最基礎的便利性,如目前已完成的《嘉興藏》正續編,是歷代藏經中,包含有最多清代以前的中國佛教著述的經典,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網站中共包含「藏經音、韻、義檢索」、「佛學多語詞彙檢索」及「CBETA佛典語文研究平台」三個檢索系統,使用者可以透過檢索工具,很快蒐集到想要的詞彙及其出處。
而「佛教文獻詞彙數位資源之建置與研究」計畫則進一步完成一些重要的佛教工具書,如《翻梵語》、《翻譯名義集》、《唐梵文字》、《唐梵兩語雙對集》與《梵語雜名》等等。數位化的辭書與佛教文獻,搭配全文標記技術後,還可以加入語言文獻的時空資訊,所以我們不但能查詢詞彙出處,還可依照年代或是其所屬藏經類別排列時間順序,甚至提供了KML檔案的下載,只要以Google Earth打開這份檔案,我們便能透過視覺化的方式觀察這些詞彙在空間位置的分佈情形,Google Earth的時間滑桿功能,也能很清楚的反映出各詞彙是何時被翻譯或使用的。
藉由這些佛典文獻的數位化以及佛典詞彙檢索應用平台,中國語言文化的演變及匯流彈指間展開,我們因此輕易地省下十年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