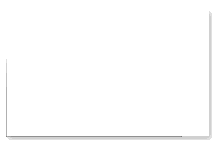通往東方的漫漫長路
文/陳泰穎
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i),十六世紀耶穌會士,於澳門等候進入明帝國傳教時隨筆。
公元1487年,葡萄牙人第一次目睹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就在短短三十年內,歐洲人的航跡就已經抵達亞洲,在遙遠陌生、價值觀迥然的東方諸國度貿易、傳播福音,在風與海的繾綣中經歷死生別離。天主教耶穌會,也在這個迷人的時空中,扮演著連結不同文明之間的角色。
由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於公元1540年創立的耶穌會,面對的是一個紛亂的時代。歐洲對希臘羅馬時代文化遺產的再發現、乃至於新教的興起,讓思想衝破固有的窠臼;印刷術的普及,則讓資訊的流通傳播更顯迅速。因此,耶穌會在創立之初,就希望神父不但要有堅定的信仰,更必須博學多聞,掌握各種專業的科學知識。
除了在歐洲的傳教之外,隨著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國家於十六世紀的全球拓殖,耶穌會傳教士也乘著季風與洋流的力量跨出歐羅巴,與一個個不同的文明相遇。不過,在通往東方的漫長旅途中,耶穌會士必須面對海上的狂風暴雨、疾病、飢餓與匱乏,以及海盜與敵對勢力的攻擊;一趟跨越印度洋、通向彼方的旅行,花上兩、三年的時間實屬稀鬆平常。
面向他者
在抵達東亞之後,耶穌會士所面對的東方,是由一個個成熟而自信的文明所組成的地理區域。如何在克服語言障礙之餘,取得和中國士大夫、日本的封建武士平起平坐的地位,進一步贏得本地社會菁英的敬重,是耶穌會最困難的挑戰與任務。耶穌會士雖然以天主教的傳教為最終目的,他們也不吝於以「遠臣」的角色,向各國君王、統治階層貢獻知識與專業技能,進一步和本地知識份子進行深層的哲學與信仰交流。
以儒士服裝打扮、替明代中國帶來世界地圖與西方科技的利瑪竇(Matteo Ricci),就是以這種平等交流的方針贏得不少文人的敬重。他憑藉淵博知識與光明磊落的人格,獲得在帝國首善之都北京居住、傳教的許可,更為耶穌會奠定在華傳教基礎。雖然因為十八世紀的儀禮之爭,天主教在中土一度遭遇禁教之禍,但是利瑪竇對中國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溝通交流所做出的貢獻,至今仍被人們銘記。
時代並非停滯不動。19世紀的鴉片戰爭讓中國門戶再次開放,傳教事業似乎步入一個新榮景。但在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當時崇尚無神論、並且對西方採取敵視態度的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耶穌會也被迫退出中國,來到本屬帝國邊陲的台灣島,繼續他們的傳教事業。
跨文化的交流
走進位於台北市辛亥路耕莘文教院內的利氏學社,木質素雅的書櫃空間中,陳列著一卷卷漢人民間宗教文獻、以及一冊冊大部頭的《二十四史》,讓人感受到一股濃厚且跨越文化的人文學術氣息。「耶穌會的傳教士通常會選擇鑽研一種與學術、文化交流有關的學科,甚至會投入到讓人忘記他是神父的程度。」利氏學社的李禮君主任如是說。
確實,從利瑪竇的時代開始,耶穌會除了向傳教對象介紹歐洲之外,也同樣關注在地的文化。「或許是因為早期耶穌會的傳教據點,經常是對歐洲人來說十分遙遠的邊界。在這些據點的所在地,歐洲人並不處於優越地位,所以我們必須要學習本地文化,瞭解本地人的心。」耕莘文教院杜樂仁(Jacques Duraud)院長,和我們分析耶穌會之所以對文化交流投注巨大心力的理由。也就在這種求知慾和傳教任務的驅動之下,耶穌會在不知不覺中,為各地傳統文化的研究保存做出深遠的貢獻。
1952年,天主教會被迫離開中國,也讓耶穌會長期蒐藏的書籍與漢學研究成果,踏上流離顛沛的命運。1966年,甘易逢神父(Yves Raguim,1912-1998)、雷煥章神父(Jean Almire Robert Lefeuvre,1940-2010)創立台北利氏學社,終於替多達五萬餘冊的辭典、佛道教文獻、史書找到落腳之處,讓更多學者、修士能夠在此接觸中國文明的斷面。1950年代之後的耶穌會,除了針對台灣漢人與原住民進行傳教工作,也頭一次有機會,將原本散布在中國大江南北的漢學蒐藏匯聚於一處,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工作。在平靜但帶著詼諧的笑容中,杜樂仁說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原本好久以來都做不到的事情,毛澤東幫我們做到了。」
知識的基礎工程
如果我們從跨文化交流的歷史角度出發,當東方與西方相遇之時,如何克服語言不通的障礙與藩籬,是耶穌會與學術工作者的最大挑戰。因此早在十七世紀開始,耶穌會士便積極投入翻譯與辭典編著的工作中,《利氏漢法辭典》(Dictionnaire Ricci, Le Grand Ricci)更是一部集眾人大成的知識寶庫。
為什麼雙語辭典的編纂工作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魏明德神父如斯寫道:「這部雙語大辭典宛如一棵樹。它像兩股巨型的根,一端深入法語的沃土,一端探進中文的沃土,同時吸取雙方的養份。」也因為不同的文化,其世界觀也會有細膩的差異,如何透過辭典的編纂,讓使用者能夠更精確掌握對方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邏輯,協助我們欣賞不同的文化,也正是利氏學社耗費半世紀光陰從事這項志業的初衷。
目前利氏學社除了東西語言辭典之外,也在天主教輔仁大學和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協助下,進行資料數位化工作。在今年的計畫期程中,利氏學社完成了早年所藏甲骨文、漢人宗教、語言等主題學術研究報告總共319筆文獻的數位典藏。由於耶穌會本身是一個國際化的組織,在工作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就是準確判讀這一篇篇使用法、英、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多種語言的文獻,同時在龐雜史料、書信中考據出作者生平,替使用者留下完整的脈絡與線索,提昇後設資料的品質。因此,如果說利氏學社進行數位典藏,是一場不出田野的知識考古學研究,雖不中亦不遠矣。
無論是造訪實體圖書館,或是瀏覽資料庫網站查找資料,都是人們使用知識的方式。不過,妥善保存高達五萬冊的圖書文獻、辭典編修乃至於傳教歷史主題典藏,對民間非營利組織來說並非易事。近年來,利氏學社也分別與國家圖書館、國立台灣大學、天主教輔仁大學、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合作,在實體與虛擬的世界中打造一個典藏與交流的平台,也協助對漢學與天主教傳教史有興趣的朋友,能夠接觸這批寶貴的史料。由於1950年代傳教重心轉移至台灣,因此除了早期的漢學研究成果之外,耶穌會與利氏學社也和台灣原住民結緣。未來,利氏學社將把目光投向太平洋,協助世人瞭解南島語族的語言與文化。
夢一般的海平線
法國歷史學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回顧中世紀歐洲歷史時曾寫道:「對於中世紀的西方來說,印度洋富有異國情調,是西方人追尋夢想和宣洩感情的寄託。」當貿易船往那夢一般的海平線航去,隨船前往東方的耶穌會神父,或許在心中也是百感交集。
不過,「利瑪竇與耶穌會,在當代中國與歐洲的知名度和觀感,其實有著很大的不同。」語重心長的杜樂仁替讀者解析這段弔詭的歷史。在歐洲,利瑪竇只是到東方的眾多神職人員之一,又因為耶穌會深刻地涉入政治與宗教上的紛爭,在歷史上留下一些爭議;反而在華人社會,利瑪竇與耶穌會由於在東西交流上所扮演的角色極為成功,他的故事即使是中學生也能朗朗上口。至少,在遠隔家鄉千里之外的異地,耶穌會找到了存在的價值與認同。
也許是因為千百年的慘痛犧牲,經歷宗教戰爭與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深刻體認到「寬容」與「深層對話」的重要性。在杜神父所創辦的《人籟》雜誌中,我們經常可以讀到擁有不同宗教、種族、文化背景的知識份子,在這平台進行理性思辨。這種跨文化的對話,或許可以追溯到四個多世紀之前,當耶穌會神父踏上通往東方漫漫長路的那一刻……
編註
台北利氏學社
1966年由甘易逢(Yves Raguin,1912-1998)、雷煥章等耶穌會士所創立。其名「利氏」乃為紀念四百多年前赴中國傳教的開拓者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初期,學社致力於探索中國文化、宗教與社會,在國際漢學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並從中發展出辭典編纂的使命。歷經五十餘年的努力,利氏學社出版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利氏漢法辭典》(Le Grand Ricci)及其他多種雙語及專門辭典。自90年代起,利氏學社的研究方向逐漸轉移至台灣研究(如原住民語言、文化及宗教),以及對永續發展、文化多樣性與心靈培力的關注。2004年1月,學社創辦《人籟論辨月刊》(Renlai Monthly),次年創辦「e人籟」(www.erenlai.com),以創造台灣與亞洲知識份子、草根團體與決策者之論辨與行動平台。近年來,學社更致力推動跨領域之太平洋與南島文化研究,並與國家圖書館共同協議成立「利瑪竇與太平洋研究圖書室」,並將部份館藏移轉至國家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