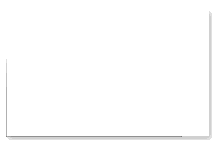台灣「外省人」生命歷程之多重記憶─私人與公共的接縫
文/張茂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大多數人說臺灣的「外省人」族群,指1945年9月之後到1955年大約十年間來臺的大陸各省老少人士以及他們在臺灣出生的後代。合計在此期間抵台的人數估計約百萬人,其中又以1949年六月之後到1951年之間抵台人數最多,約占了90%,其中包括號稱「六十萬」的大軍(這只是宣傳的數字)在內,而估計當時來臺軍人中有八成是屬於單身無眷來臺(但不一定為未婚)的男性。
戰亂將一群背景混雜的人推向臺灣,他們之中上有國民黨國高官顯要,包括上千位的中央民意代表,沿海諸省資本工業家,中層有流寓文人、小資與知識青年,下層又有流亡學生、大批(或被迫或志願)從軍的士官兵、大陳撤退軍民以及中南半島孤軍與其眷屬等。在這個「軍民同胞」複合體系之外,還有1950年、60年代間被剝奪基本公民權利的政治犯,他們來自大陸各地,因為各種原因而被整肅、槍斃或判刑坐牢的受難者。
二、歷史現實與矛盾的結
說到外省人分布的籍貫(省籍),也是中國大陸東西南北都有,雖然以南方以及沿海諸省像江蘇、浙江、四川、湖南、山東、廣東、福建等地的人佔了相對的多數。在進入1956年之後,因為「中(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方面戰火逐漸遠離台海,另外一方面因為人類渴盼親密社會關係與生殖的共同驅力,單身在台的外省男性和本地婦女共組家庭成為普遍的新人口現象,這就是今日臺灣外省第二代多是「芋頭蕃薯」(父外省、母臺灣)的歷史與驅力。
面對這樣複雜的人口與歷史現實,現在大家常把「外省人」當成一個方便的「族群」用語確實是有疑議的,所以我常將這三字把放在括弧裡。其實「外省人」作為一詞彙,有兩個語言的背景:第一個背景是中國沿用很久的「籍貫」制度,第二則是與之相關的關於祖先來源的父系社會想像。前者規定了地方與統治者之間的臣屬位置,統治者得據以區分並管理人民,依籍貫派遣人民勞役、抽賦稅、辦科舉以及遂行中央政府對於各地方的統治。而後者則為人民對於祖先來源的空間聯繫與文化想像,不同的祖籍的群體據此彼此區隔劃界,進行分工合作,也可能進行衝突甚至械鬥。所謂籍貫、祖籍的差異,經常會搭配上語言、信仰傳說、儀式、血統、階級地位的差異,這讓籍貫的分化、籍貫的意識顯得更具體、更容易覺察。
「外省人」作為一種通稱的分類法,並不是臺灣所特有,在中國大陸對日戰爭時期,四川省湧進了大量的「下江人」,當時稱他們為「外省人」。又如現在在中國境內戶籍制度仍然非常重要,而在沿海以及各都會因為招募外省市的剩餘勞力,都有關於「外省打工群體」的說法。而臺灣的「外省人」的用法之所以出現,確有其特殊時代背景。一方面民國政府普遍傳承了清已降的中央對地方的籍別治理,一方面則沿用日本在臺灣推動的戶籍登記制度。所以,在臺灣立刻出現了「臺灣省籍」與「非臺灣省籍」的分隔」。而1945年九、十月間雙方初次接觸,隨即因為期望落差以及涉及到權利與尊嚴的衝突,出現「省籍隔閡」,演變為現在「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群體分類的開端。光復十個月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繼之軍隊鎮壓、白色恐怖與威權統治,大中國與臺灣獨立主張的衝突浮現,數十年間促使「省籍隔閡」以至於日後的「省籍矛盾」問題複雜化。

老兵譚力飛14歲進入黃埔軍校,為國效力一生的他不曾澆熄滿腔熱血,晚年獨居在桃園眷村。〈半生兵戎、一生掛念,此處總是歸鄉路〉,黃璽恩攝,年份:2006,桃園縣:楊梅市。圖片提供者: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網站名稱: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
三、成為公共論述的議題
台灣從1981年起已經立法廢除了戶籍制度以及所有官方文書中有關「籍貫」(本籍)登記的規定(只剩下「出生地」一欄)。而臺灣「省」也在1999年正式虛級化,是以「外省人」的想像,不但不像客家、臺灣南島民族、福洛語族,可用特殊的傳統語言、儀式或日本時代的戶籍登記來構築族群疆界的「真實性」,甚至連「籍貫」也快要從制度上消失了。同時,文化中過去對於父系血統的強調,也在性別平等、性別主流化、普遍通婚的潮流下,受到侵蝕。
但是這並不表示「外省人」的討論,作為一種公共議題,就因此停止,事實正相反。因為在1990年代某些政治取向的論述中,「外省人」先是被當成為「臺灣民族」的「族群」組成分子,被當成臺灣「新住民」加以一體平等「接納」,但也有時被當成不認同台灣本土的「懷抱中國的流亡者」、壓迫者與階級優勢者,進而排斥「外省」群體其為公民的正當性。臺灣不同政治立場人物,常在政治競爭中的口水戰中相互輕視、蔑視對方的背景,而發表帶有歧視的觀點,也讓「外省人」不得不持續成為公共「問題」,這和台灣民主程序中的總統大選,統獨藍綠,國家認同矛盾重疊。最後的結果,就是原本來源複雜互異的「外省人」面貌,一旦被吸納進入這樣的政治公共論述中,當年百萬人的境遇,歷史複雜性,日後數十年的各自路徑,以及來臺後的「外省人」庶民生活史,面貌被簡化,越來越單純與同質化。

兩岸隔絕近50年,高秉涵(左)終於在1991年回到故鄉山東菏澤,見到數十年未見的堂爺高三亂(右一)不禁熱淚盈框。〈請問你是誰〉,年份:1991,山東:荷澤。圖片提供者:高秉涵。網站名稱: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
四、數說生命的記憶
1949年後的六十年,經歷一甲子的歲月,2009年可以說是「外省人」議題公共化的一個轉捩點。這一年中共建政六十年,而1949年「勝利者」的慶祝卻無意間帶動了世人對於當時「戰敗者」的好奇與興趣,就是讓第二代人激發更願意去面對歷史中「失敗者」的「真實」。其中引起重大迴響的代表就是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以及好評如潮的齊邦媛的《巨流河》。這個轉捩點對於臺灣的特別意義,就是重新面對「外省人」庶民眾生當時可能面臨的歷史境遇。兩位作家代表不同世代,文體與文字互異,但在某一角度來說,都是不以成敗論英雄,呈現了個人的不可負擔之重和集體命運之間的牽連。從小人物的「私密」的命運,原來不重要的,去看時代的「大歷史」,也讓讀者有機會去感受他者的脆弱與堅軔。
採取同一庶民生命史觀點的「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數位典藏資料庫,於2006年亦開始透過民間團體的合作、個人的捐贈與研究者的調查,將典藏資料分成三個不同的主題:
(1)分離之情(難投遞的「家書」)與具有性別觀點的書寫方式(「女書」)
(2)被遺忘的外省人返鄉運動與「山東流亡學生」
(3)用對照的地景呈現的外省人的不同處境(熱血青年被處死的異鄉埋骨地與大陳義胞的信仰地易地興旺)
這裡沒有大人物,沒有英雄豪傑史,卻有足以觸動反思行動並教人油生感佩、感念、感慨的議題,也就是在私密與公共論述間那條常難以訴說的情感與記憶的接縫。我們人正因為有記憶, 才有存在,我們也因為有情同感,才有理解與諒解的能力,因為有過去,才能面對未來。

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發起返鄉運動,要求政府發放每位老兵新台幣六萬元返鄉探親路費,以實現照護老兵、榮民的諾言。〈「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傳單1987-11〉,年份:1987。圖片提供者:何文德。網站名稱: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