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典藏與我的家族
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專任助理 陳泰穎
因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一日假期,因此在冬春之交的慵懶午後,我有機會攤在家裡,懶洋洋地讓各種思緒奔馳而過。不期然地,我突然想起了以前,媽媽曾經提過的名字:「王超倫」。他不是甚麼名人,只是一個沒有機會把國立台灣大學念完、就急急忙忙離開人世的年輕人,因此在大部分的台灣歷史辭典裡面絕對不會有他的資料出現。他在1950年時離開人間,至今已經有五十八個年頭了,但是他在我母親的家族當中,卻是一道已然超過半個世紀、至今依然存在的深刻傷痕。我原本以為,世界和我想的一樣,早就將他忘卻;但是當我嘗試利用網路搜尋引擎,不抱期待地打進他的名字之後,事情卻不如我所想的那樣悲觀,一筆王超倫的搜尋結果,赫然出現在數位典藏聯合目錄、來自國史館的資料頁面上頭。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ContentID=7847&CID=16991&OID=1428324
王超倫,是我外公的兄弟的兒子,如果今年還在世,也已經是八十多歲白髮蒼蒼的老人家了。我還記得我的母親第一次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我還只是一個高中生;而王超倫過世的時候,也才不過是二十四歲、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四年級的學生而已。他和那時候許多念理工的人一樣,除了數字與公式之外,對於世界運作的方式更有深刻的興趣,而對於社會也抱持思索的好奇與廣博的同情心。在1940、50年代之交的台灣,正是經濟凋敝、政治趨向威權體制的年代,社會上有太多的紛擾與動盪,或許身為台大生而熱情的他,除了希望能夠用工程來帶給人幸福之外,更希望能夠用思想與行動的力量改變社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那時的台灣,剛剛走過了二二八事件,傷口仍然隱隱作痛。而國民政府對於社會與經濟上的問題,似乎也無法做出有效的處理。物價高漲,而在中國大陸上政治與軍事的全面敗北,更使得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台灣」口號聽起來像是一個似乎可以預見、也可以被實現的政治預言,人心浮動而期待變化。也許就在這種氣氛中,王超倫加入了具有左傾思想的讀書會,也可能憑著一股血氣加入了當時眾多示威遊行的行列。又或許,他為了他想要追求、實踐的社會理想,加入了某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也說不定。又或者,他其實只是個帶點熱情、喜歡打抱不平、批評時政的年輕人。又或者,他不小心跟人結了冤仇,所以被羅織入獄。又或者,他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場合,有破案壓力的特務又剛好必須要交差了事。今天的我,已經沒有機會再向他本人求證,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因為歷史和他的生命都已經不會重來了。唯一有跡可循的除了家中長輩的記憶之外,就是那一個個映在筆電螢幕上的細明體字。在網頁上,國史館的典藏裡面,是這樣描述他的:
「王超倫,二十四歲,臺北市人,臺大工學院四年級學生。三十七年四月,由該校王匪子英(後歸案自新)吸收,參加匪黨,直接受匪幹陳水木領導。煽動同學鄭正忠、黃獻鎮等參加匪黨組織,受命擔任匪黨「臺大工學院支部」書記,並領導該院黨徒張坤修、孫進丁、葉雪淳、陳子元等,利用該校學生自治會掩護活動,積極為匪宣傳,從事「學運」工作。其後轉由學委楊廷椅統一領導。」
在這份檔案中,王超倫被認為是叛亂犯、是共匪外圍組織派的成員,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顛覆政府、擾亂社會安寧。無論如何,在報告書中,情治機關詳述了這個組織成員的「罪狀」、發展組織與成員間聯絡的方式,提出了未來應該加強在大專院校偵防工作的意見,還讚揚了共同偵破本案合作單位的團隊精神。
這份檔案中並沒有詳述這些二、三十歲年輕人的下落。他們在五月被捕,而在六月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協防台灣海峽,阻斷了共產黨政權在1950年完全解決國共內戰與國民黨政權的如意算盤,也穩固了當時台灣的局勢。但是,鐵窗外局勢的安定,並不意味鐵窗內的人們就能夠得到一線生機。經過六個月的羈押之後,這批年輕人在1950年11月29日,被綁縛、押往馬場町槍決。
接下來的事情,並沒有被記載在歷史裡面,而是只能存在於王氏家族的記憶幽暗處中。超倫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家中未來的希望,儘管老父也曾努力經營奔走,但是經歷六個月的營救後、愛子仍遭槍決的命運,徹底擊垮了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曾經想要透過各種方法申冤,但是這種叛亂犯的案子又有誰敢承擔呢?他的父親也曾異想天開,覺得只要當上地方父母官,就能夠為自己的孩子洗刷冤屈。聽我的媽媽說,這位傷心的老父親開始試著參加地方性公職與民意代表的競選,但是在那個年代裡,有誰敢不支持執政黨推出的候選人呢?一次次的競選也就代表著一次次的失敗,而他的家產也就因此消耗殆盡。這或許也就是這位老父親在痛失愛子、社會卻又無能為力的情況之下,所採取的慢性自毀作為吧!他想向社會大聲抗議,但是時代的巨輪卻無情地輾壓過來…孤單的老父親終於抑鬱以終,只剩下王超倫與他的遭遇,偷偷地在王氏家族裡面代代口傳。
白色恐怖與二二八事件的檔案,經過了數十年的噤聲與塵封,才逐漸地向公眾開放。而在事隔將近半個世紀之後,這一個在時代中如同散落花瓣一般消逝的年輕人的遭遇,才逐漸攤開在陽光之下。我相信,這份文件的內容,在當時可能屬於機密文件,王家人和那位老父親雖然知曉孩子的遭遇,但卻應該從來沒有機會閱讀過當時情治單位的報告全文。連我,之前都沒有想過會在國史館的數位典藏當中,查閱到這位無緣長輩的資料。我相信,家族中的長輩們,看到這份檔案裡的文字,應該會有非常深刻的感觸。
也許經過了幾十年的春夏秋冬,歷史的傷痕已然雲淡風輕,孰是孰非也許還得等到幾十、幾百年後,才能有個公斷。年輕一輩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或許也只是抱著要考試才關心、考完就可以放在一旁的態度,不再懷著執著的狂熱情感。也許這種只要忙著每日生活的態度,這種不需要抱持著革命解救世界的沉重責任感的生活,就是一種值得珍惜的無形平凡幸福也說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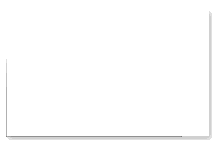





四月 7th, 2008 at 8:10 上午
數位典藏未來發展的威力實在無法想像,社會威權現像自然會淪為大眾所公斷,公義自在人心,雖然一時情境無法判定對與否,我相信未來 數位資訊全面典藏的趨勢來看,勢必可以真相大白
特別是原住民花東地區黨國概念深耕的情形來看,原住民被殖民,統化,被迫絲亳思考沒有綠色地帶,且安逸於一點點的甜頭,就淪為國黨達到政治手段的工具,唉每到選舉就是選舉部隊,選後依然放著爛,普遍遍鄉敬黨愛國的原住民都是嚴重極落後的地方,教育普遍都是極底….當然一滴酒精水, 再加上雞油的潤滑..就可以滿足的心態, 就此永遠服順於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教條之下。
數位化勢必給我們機會發出聲音的管道,部落微聲的盼望,期盼數位化是一個開始